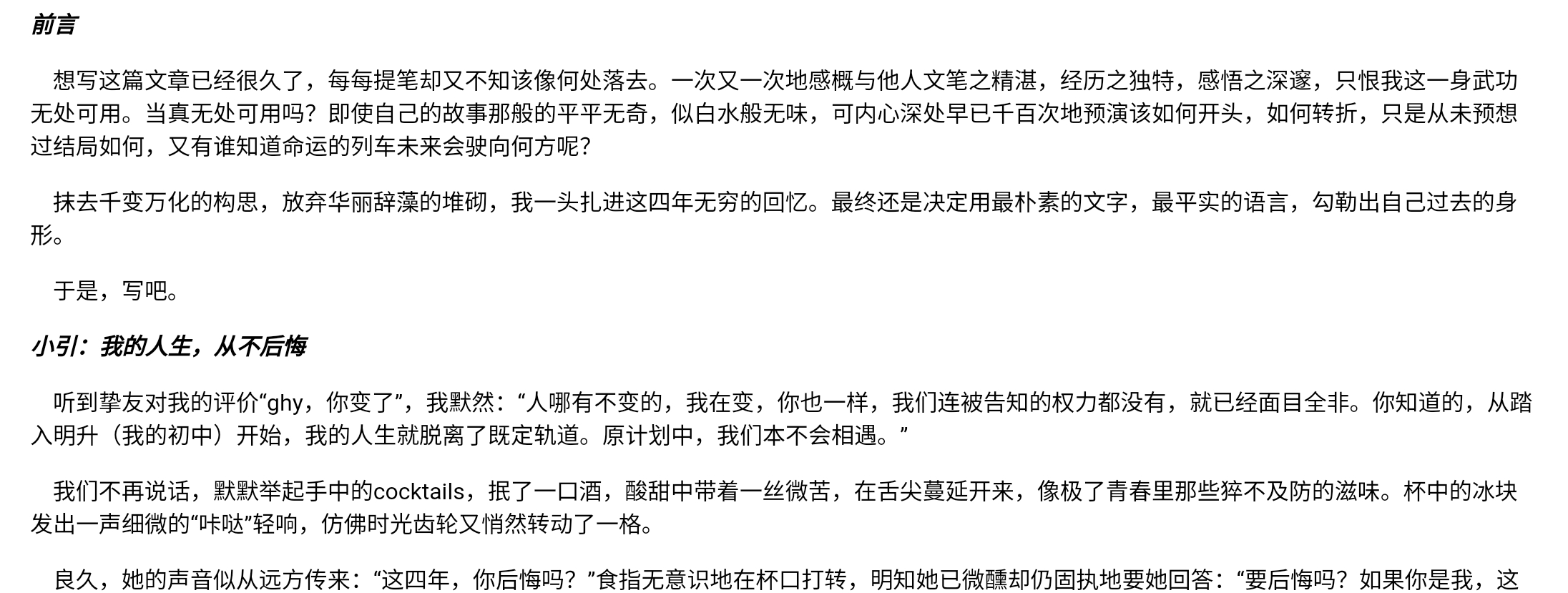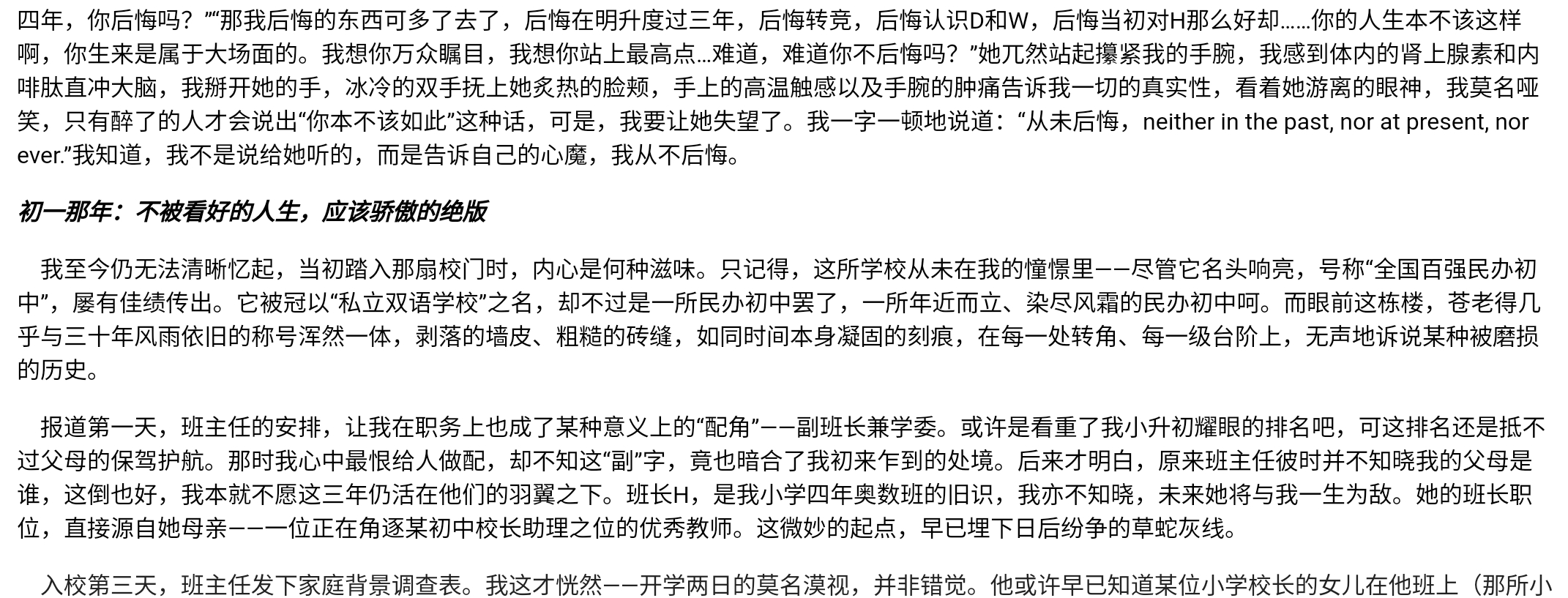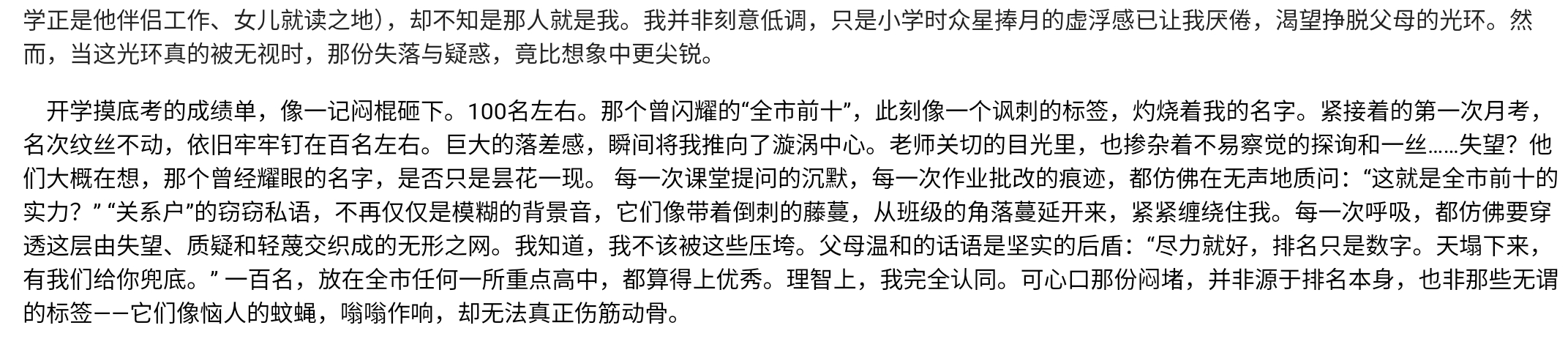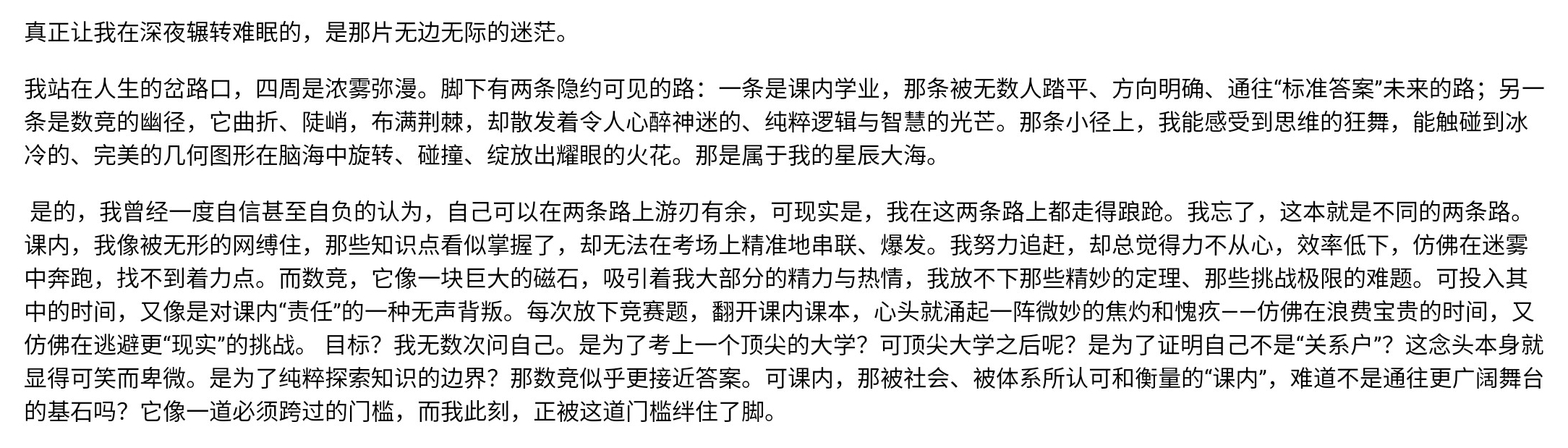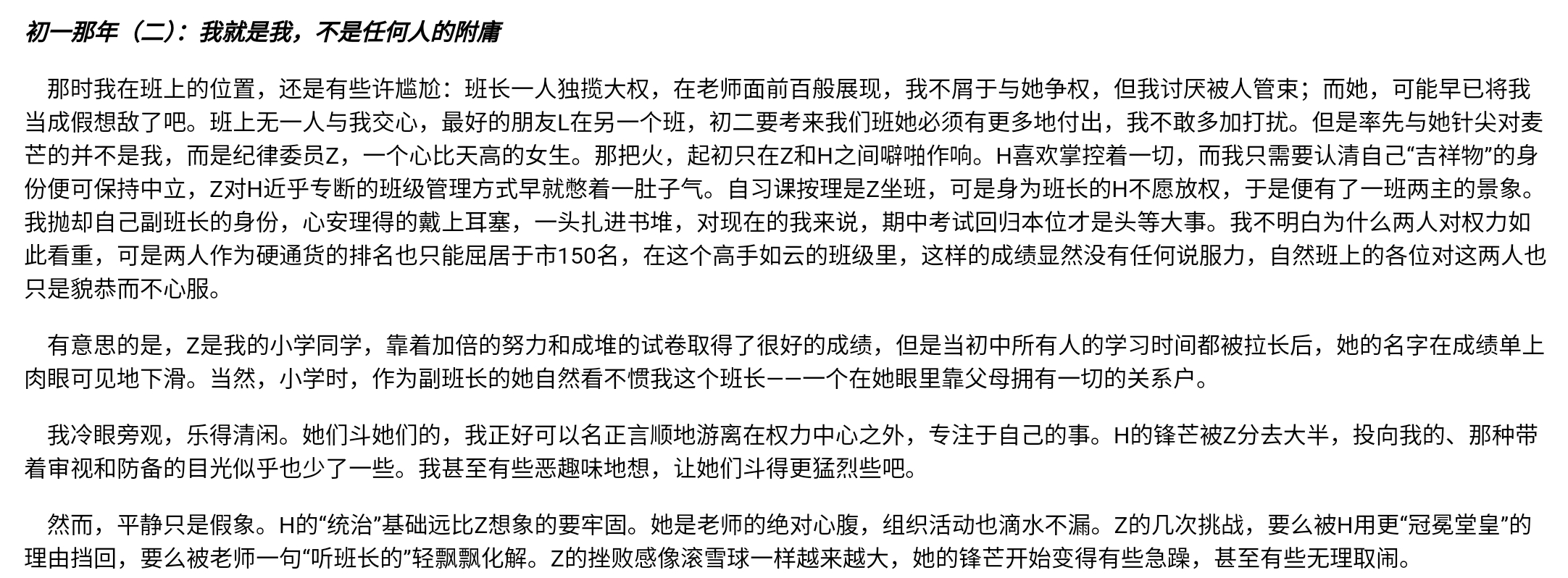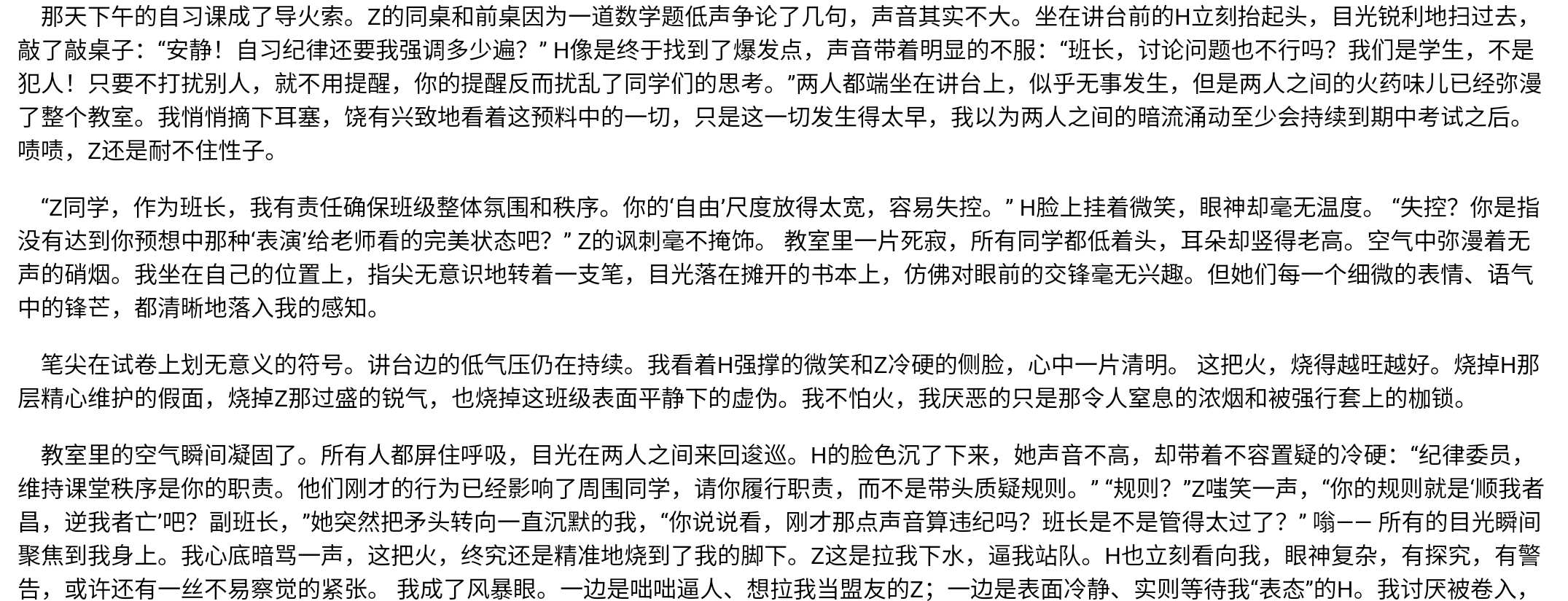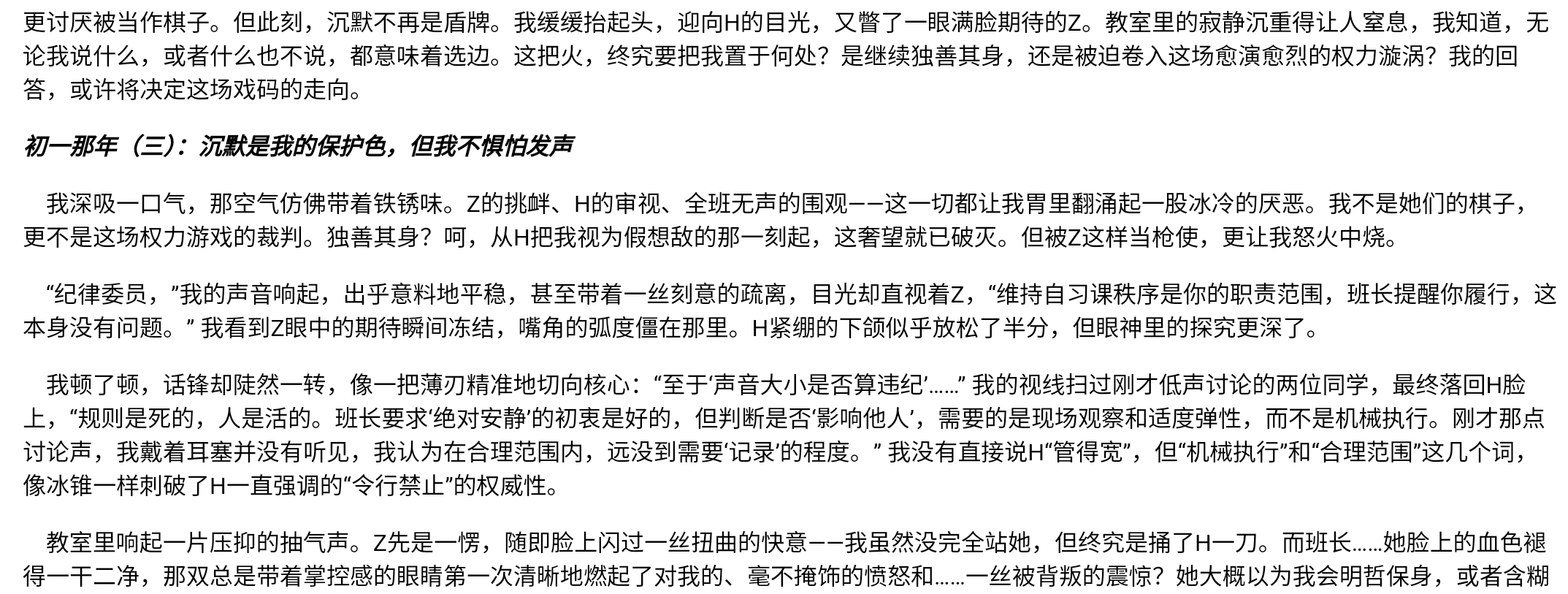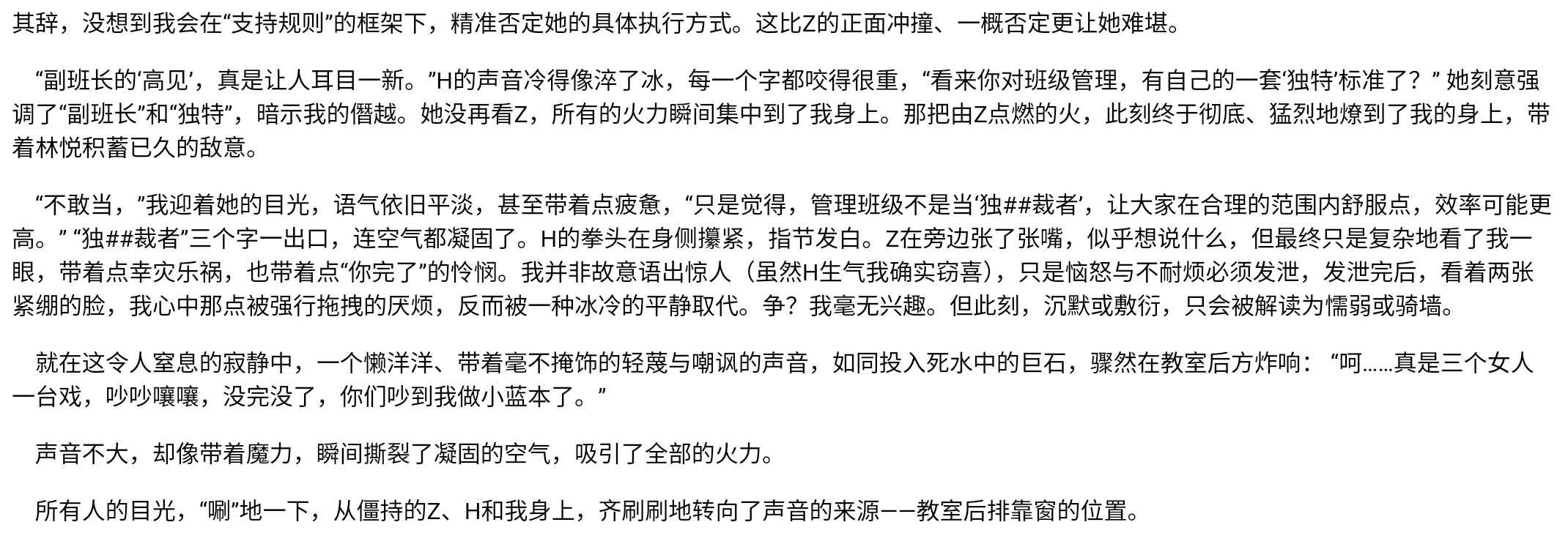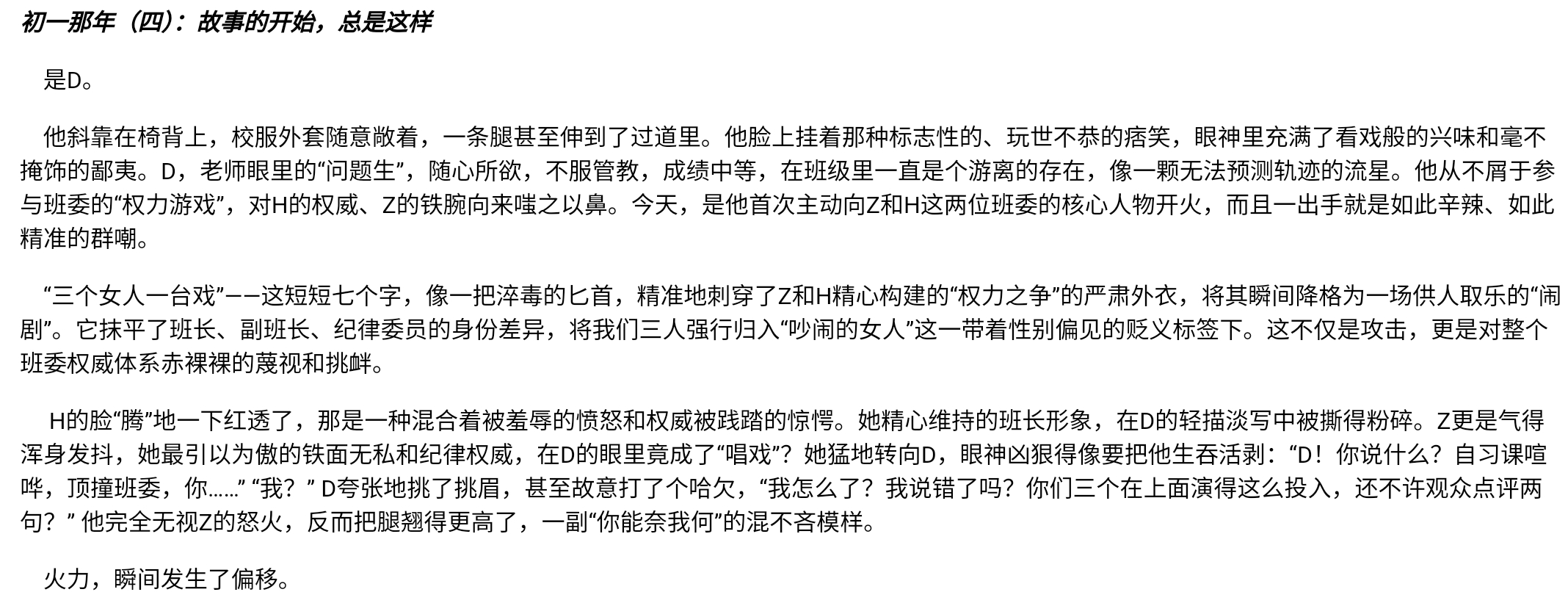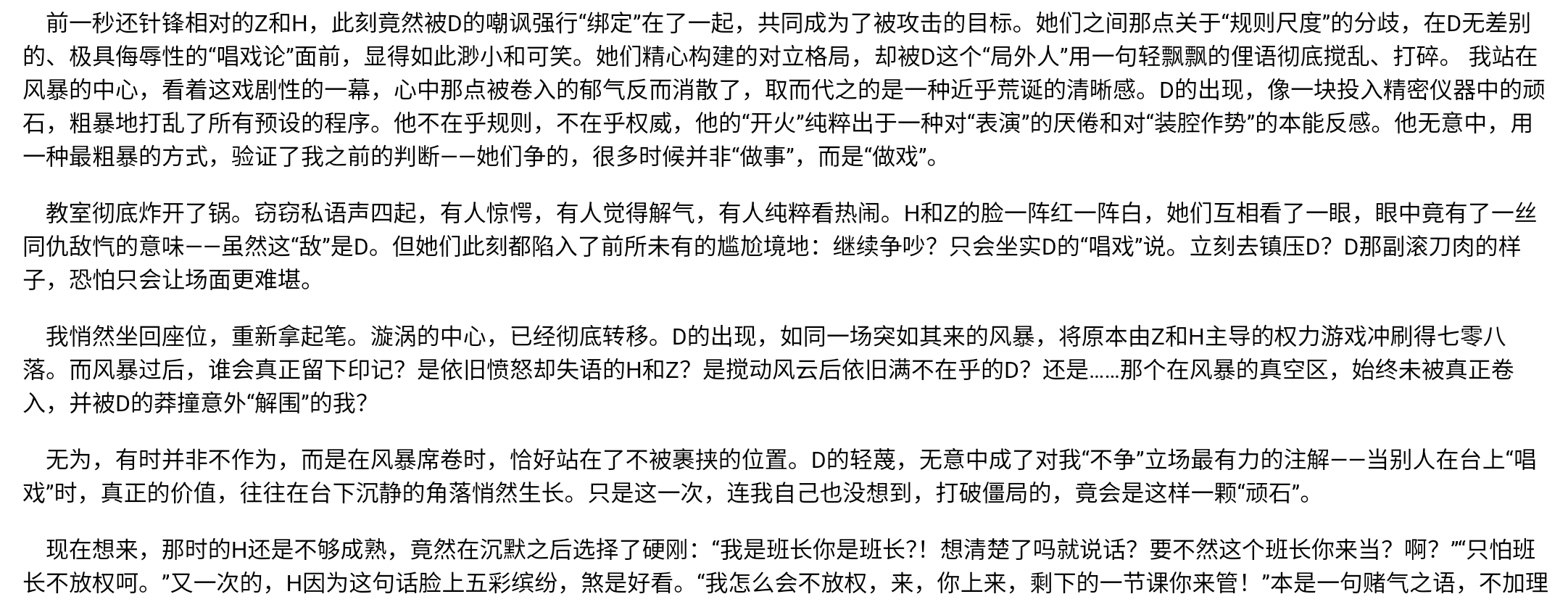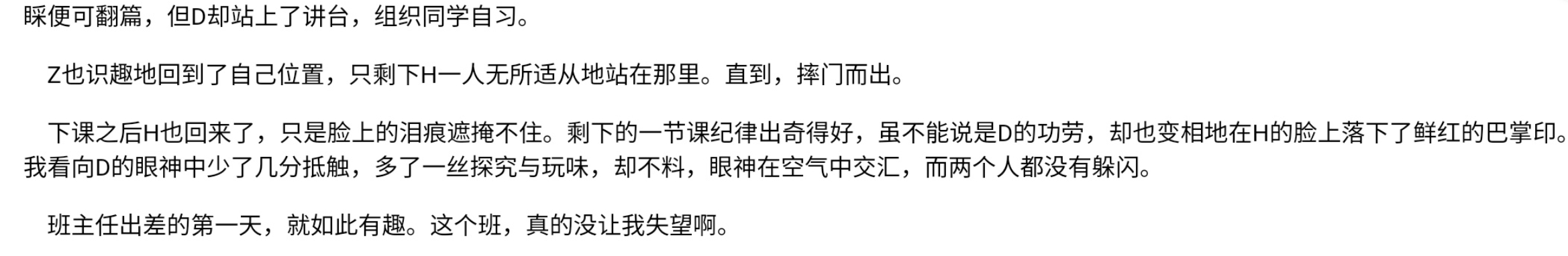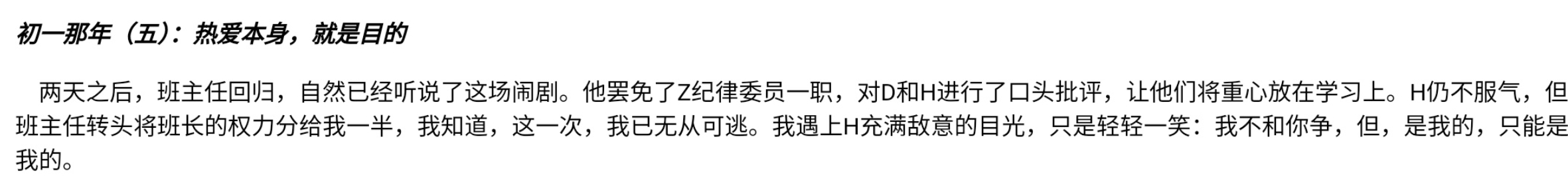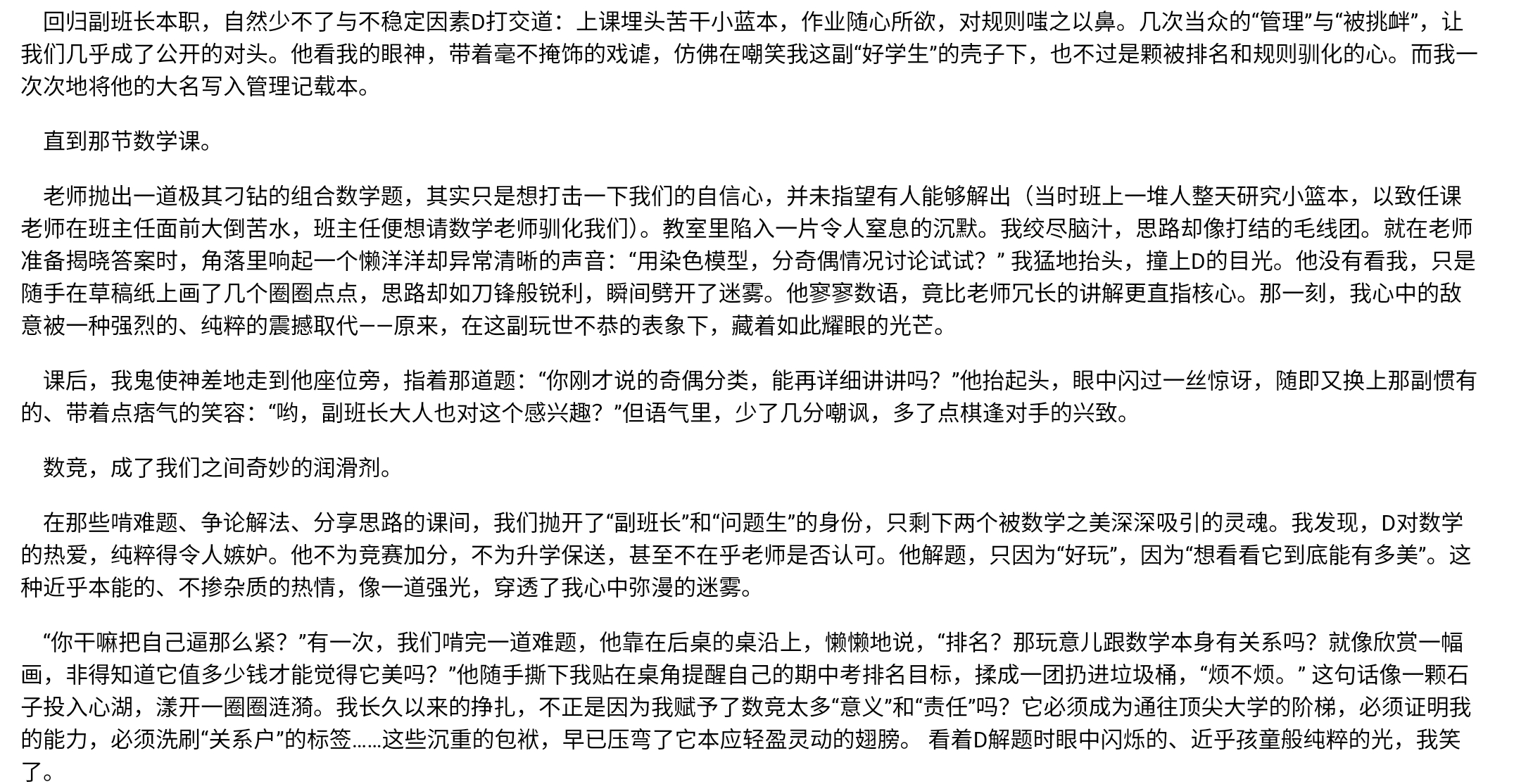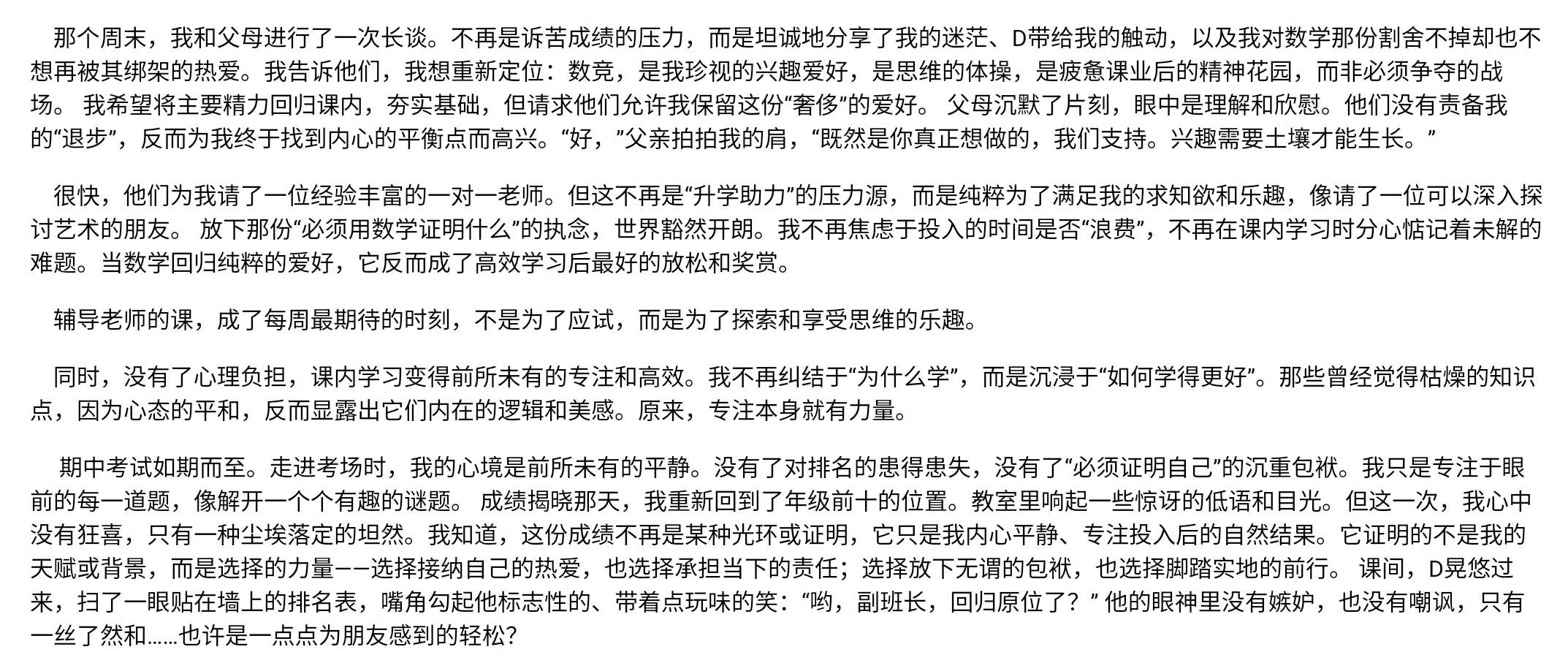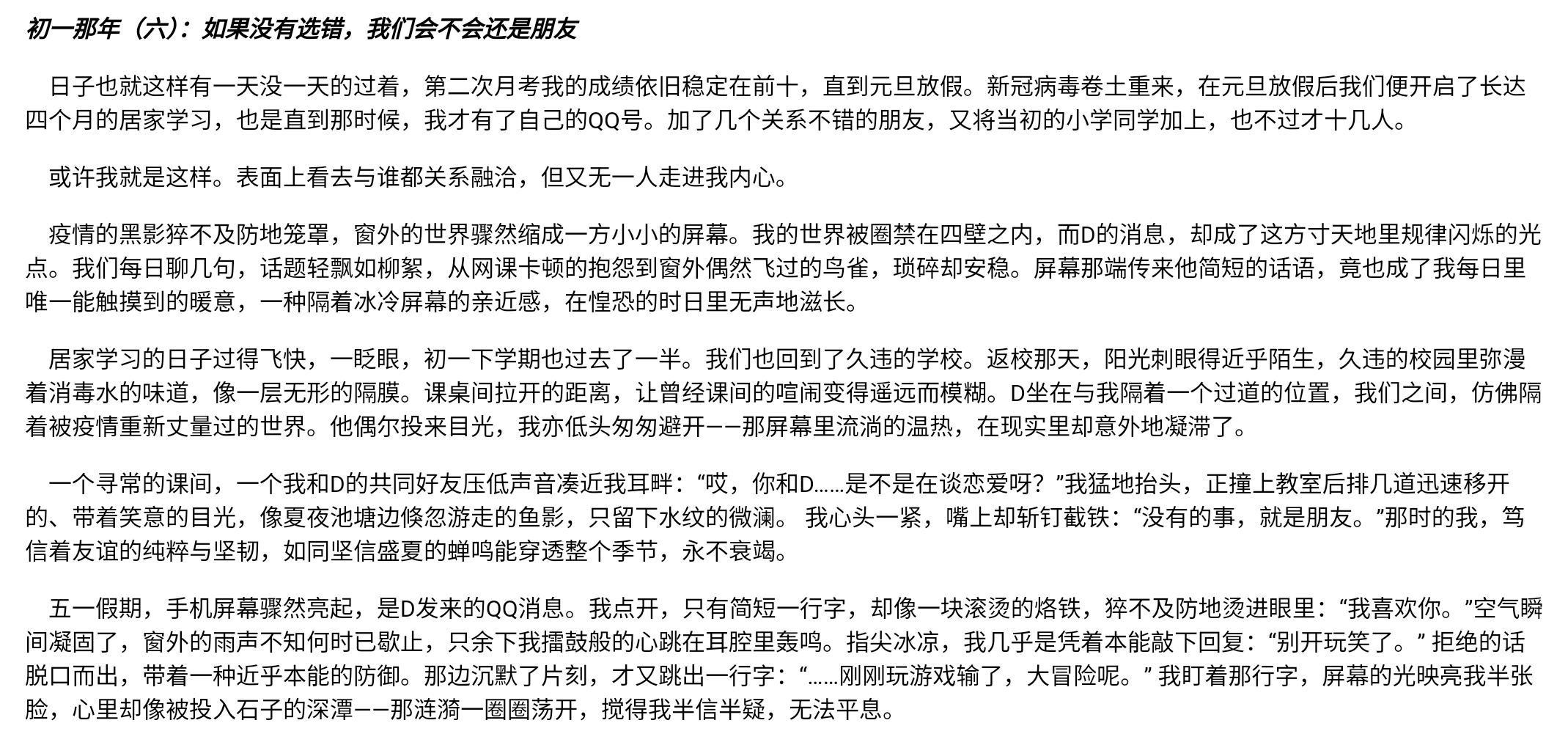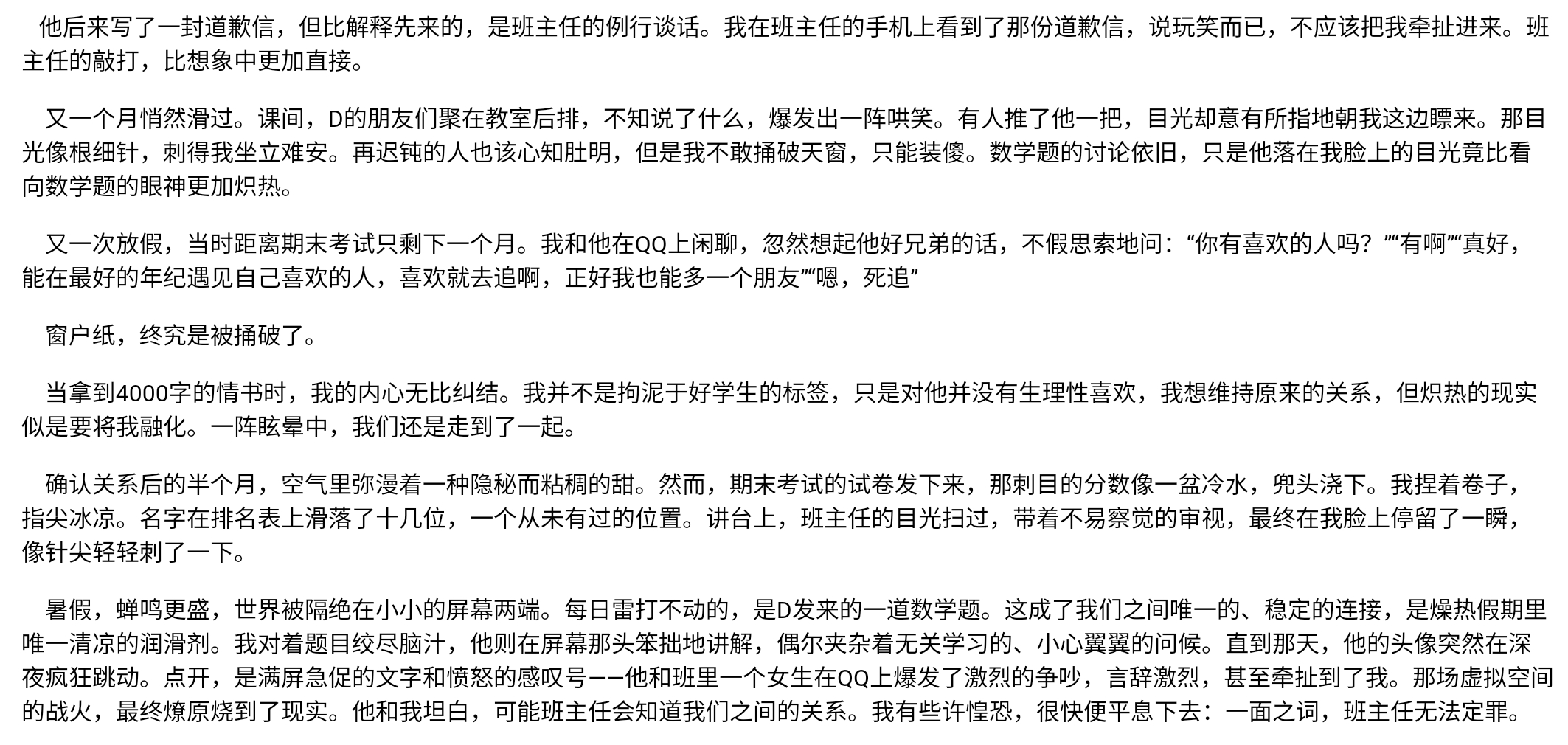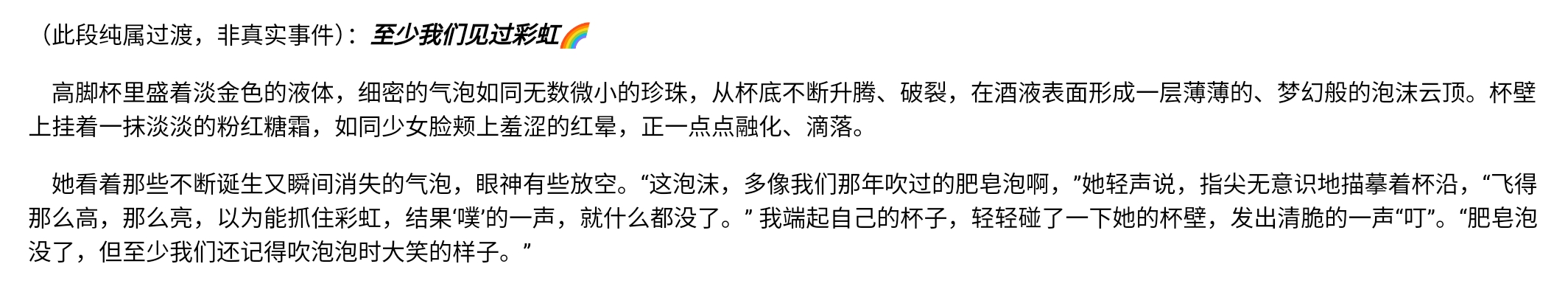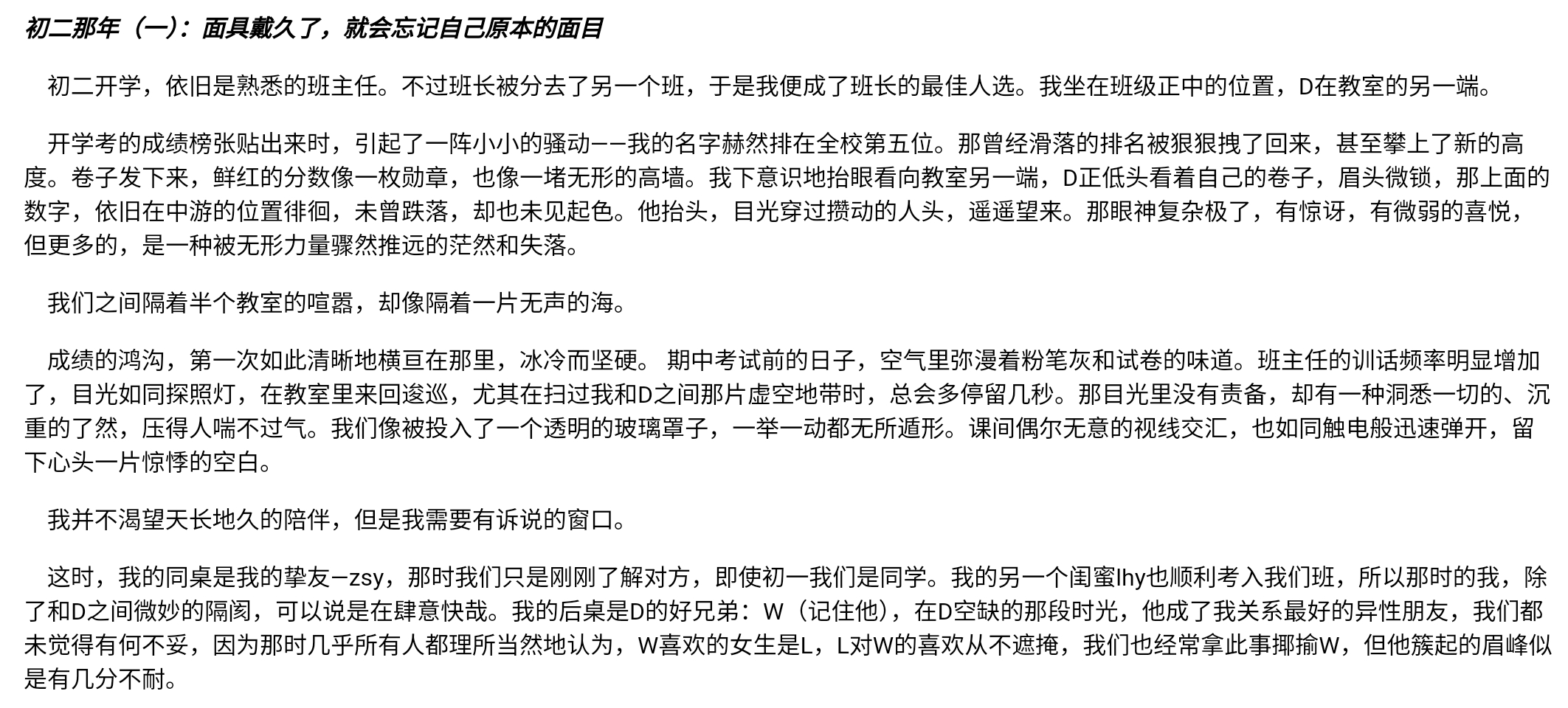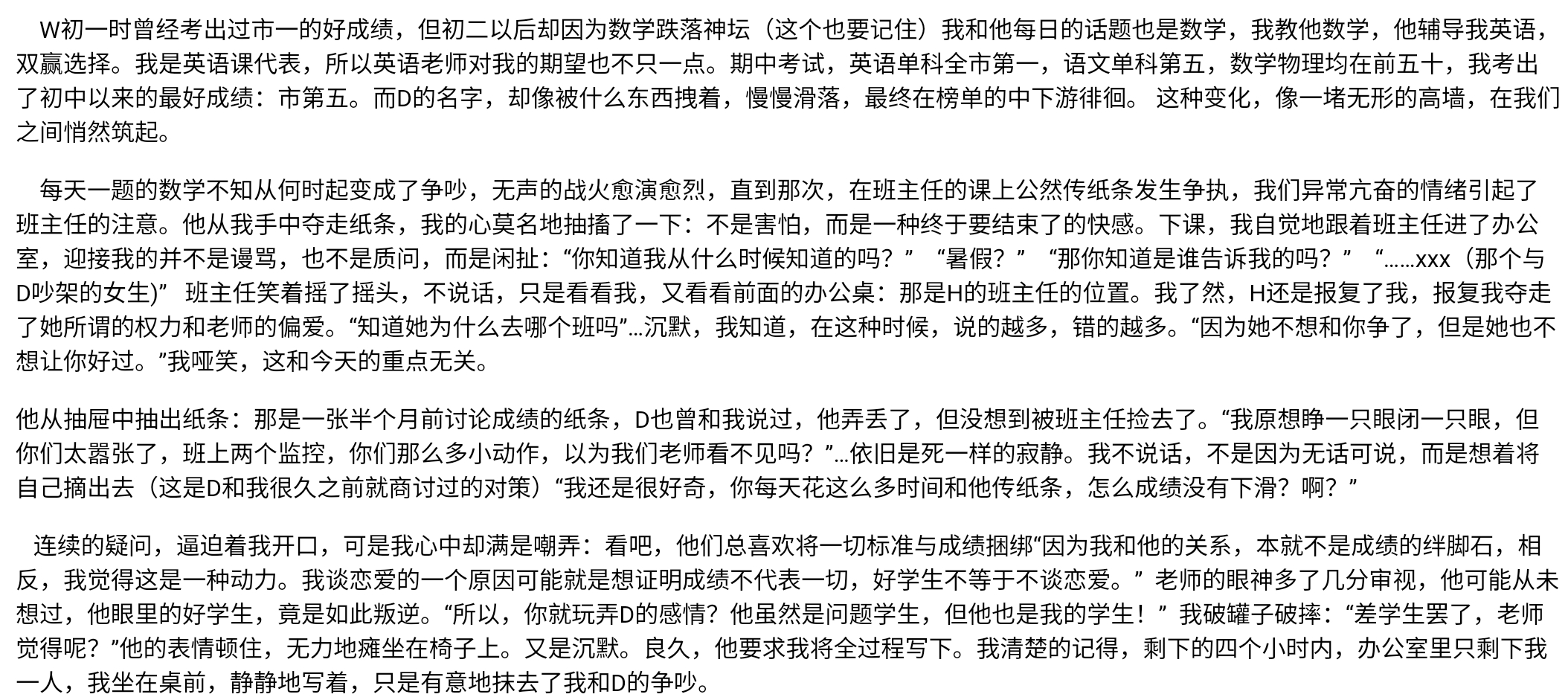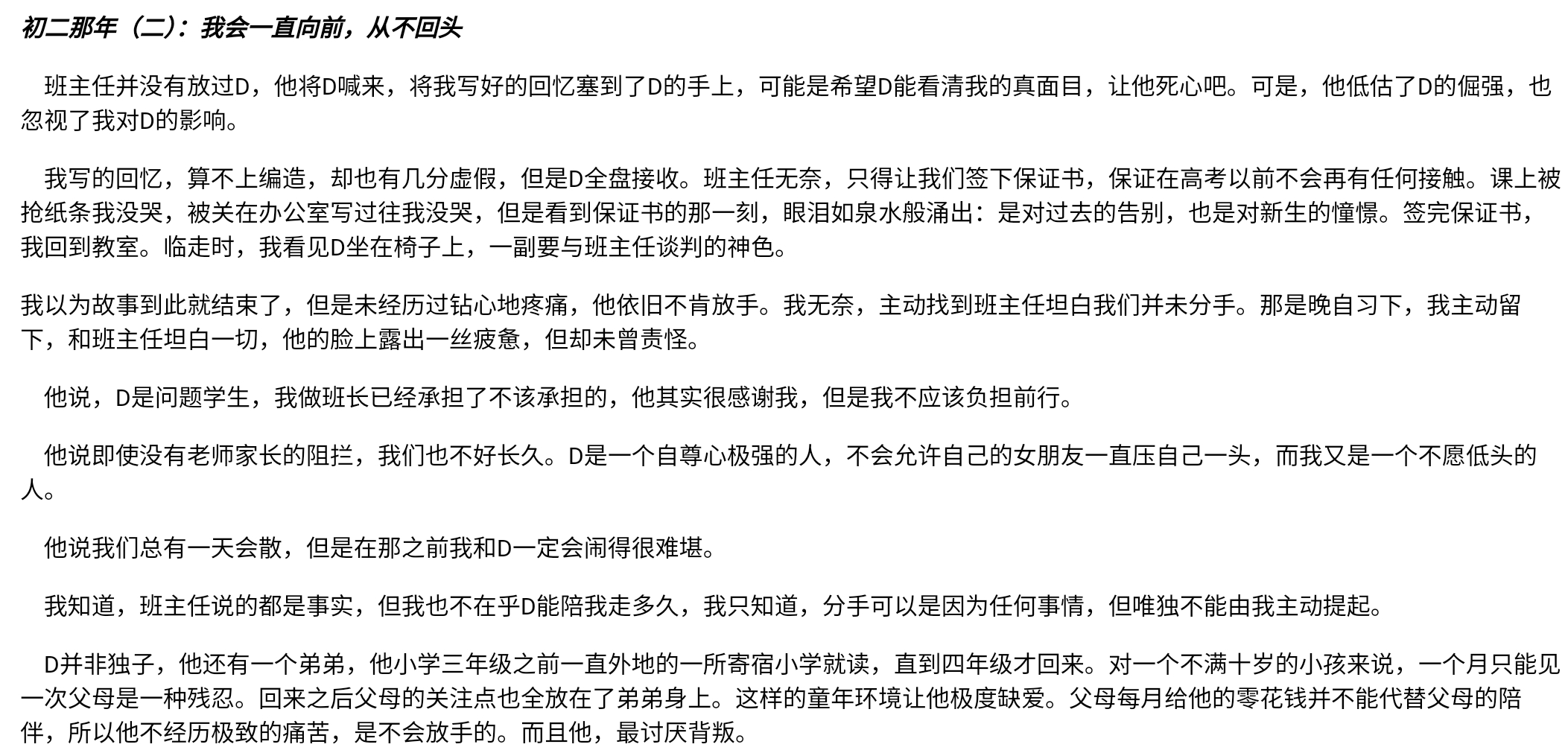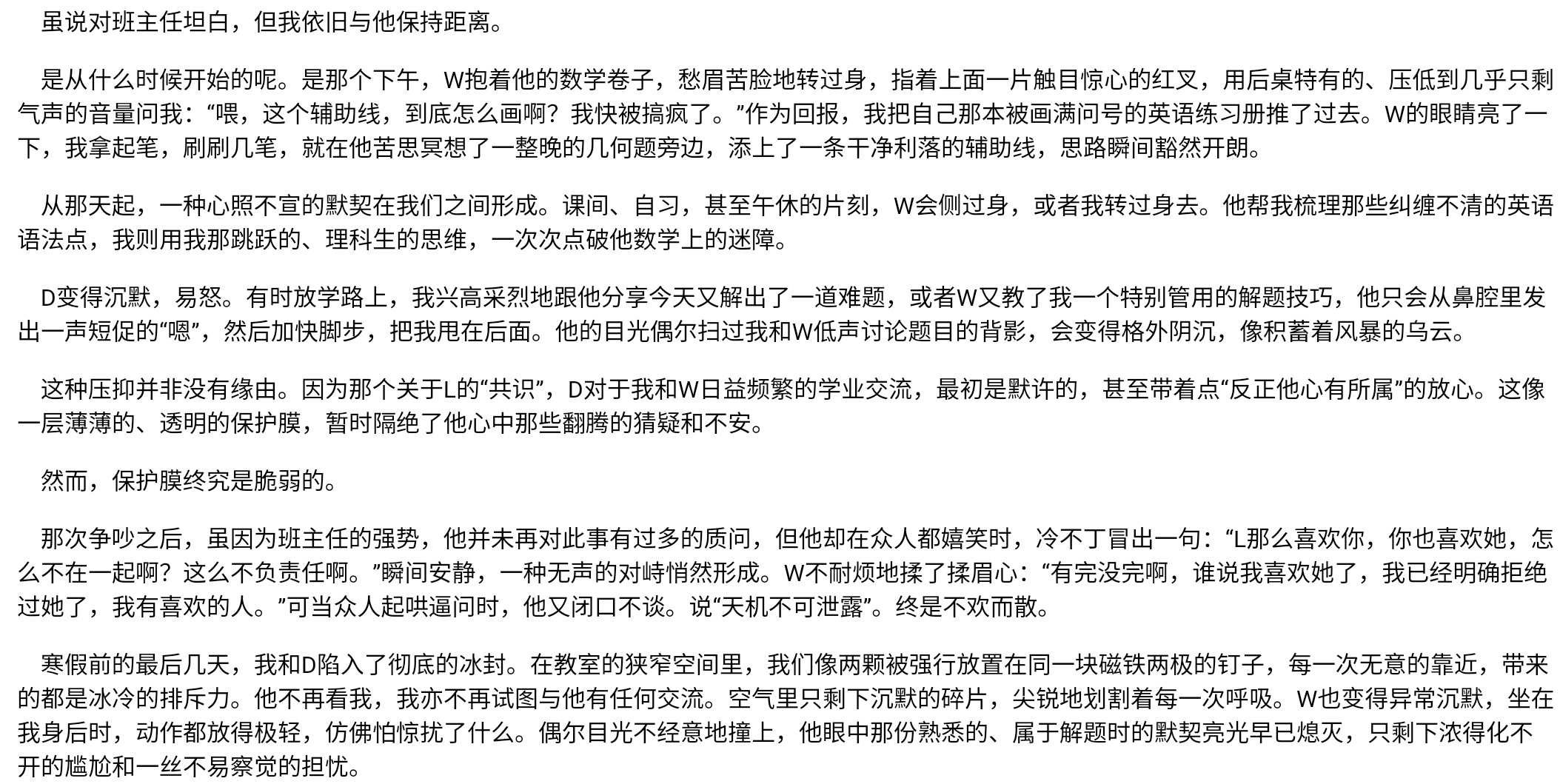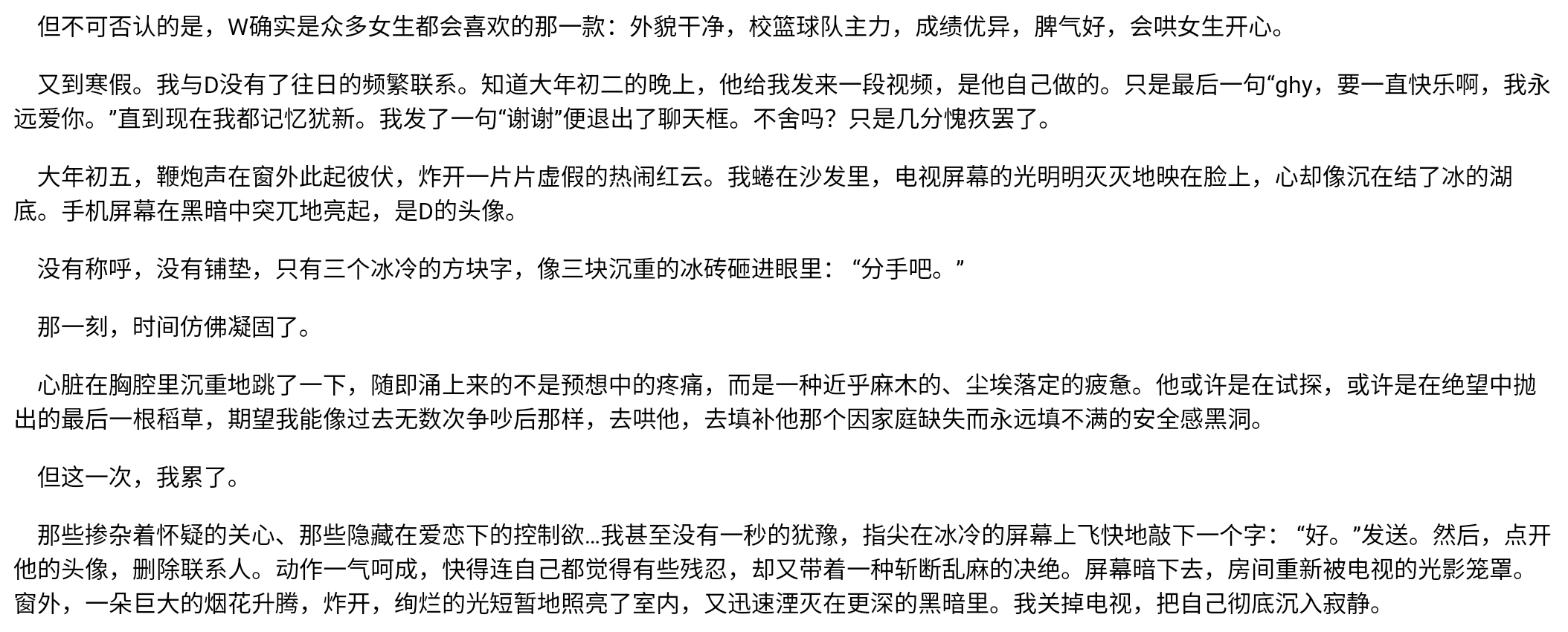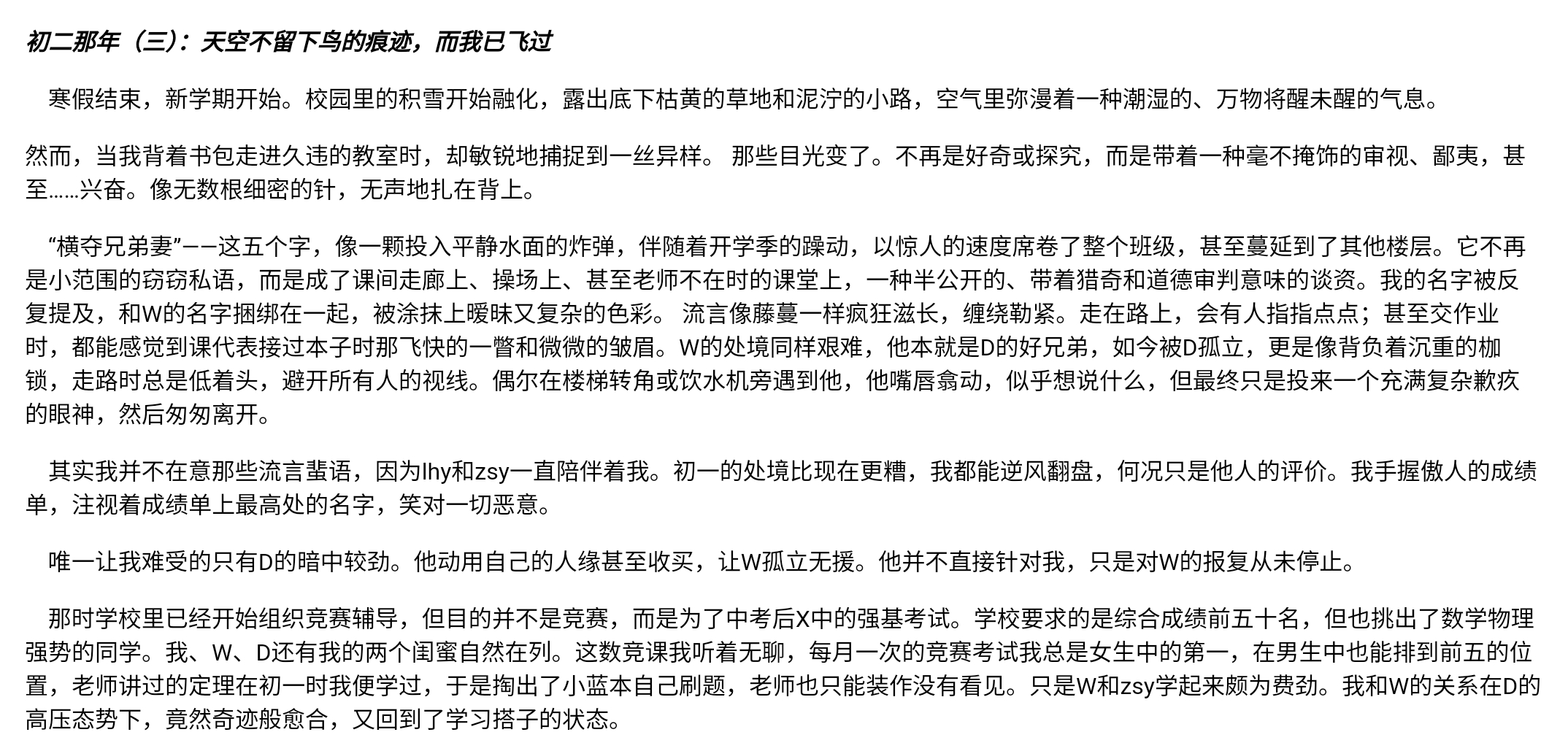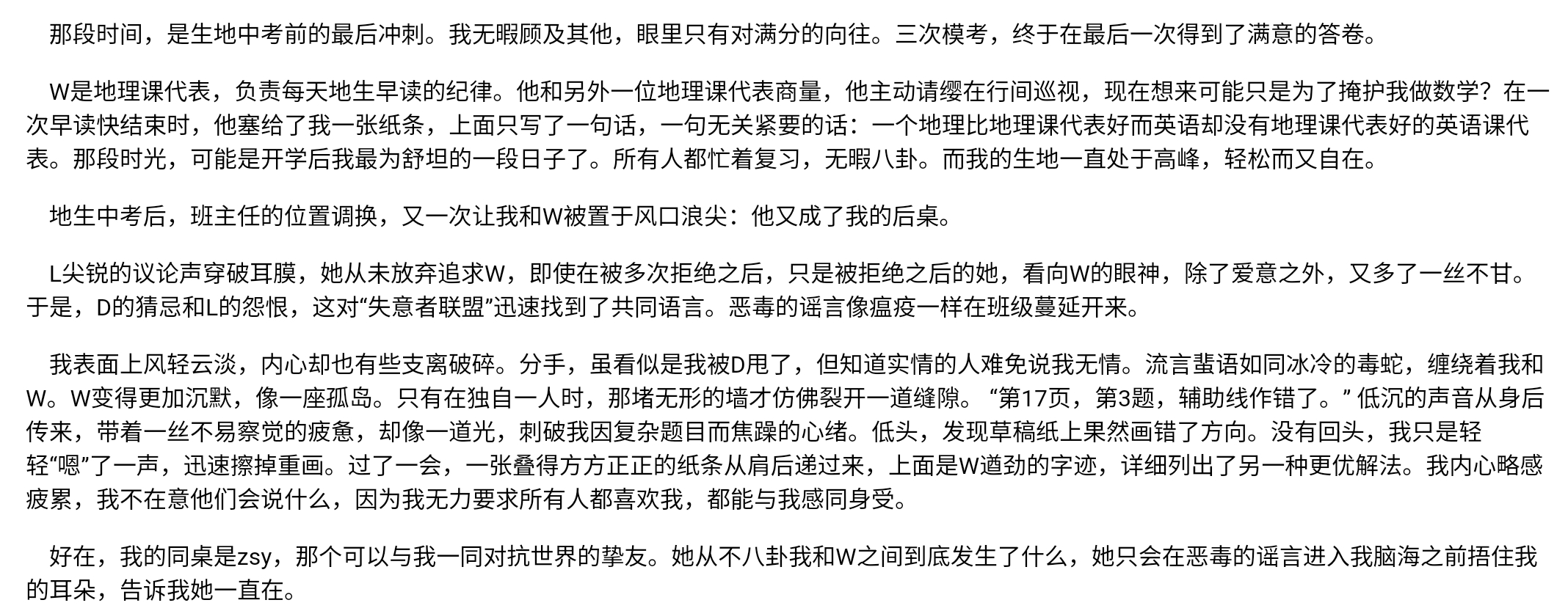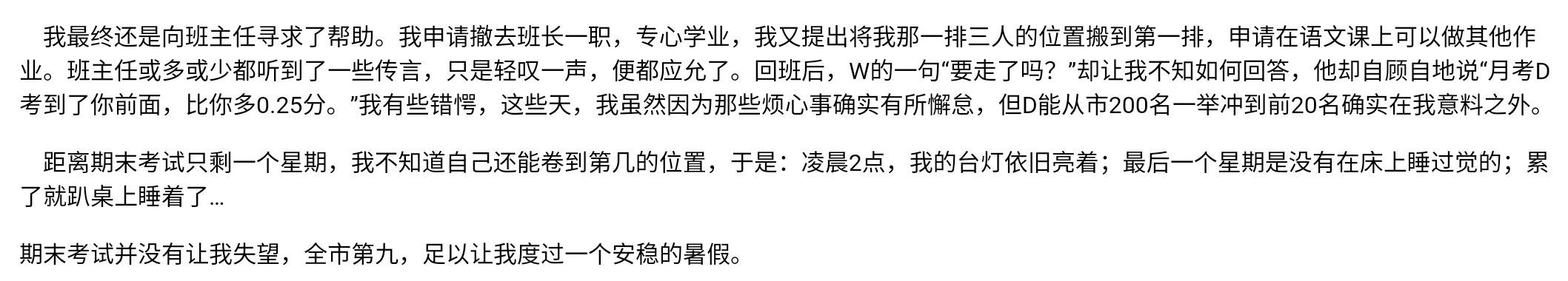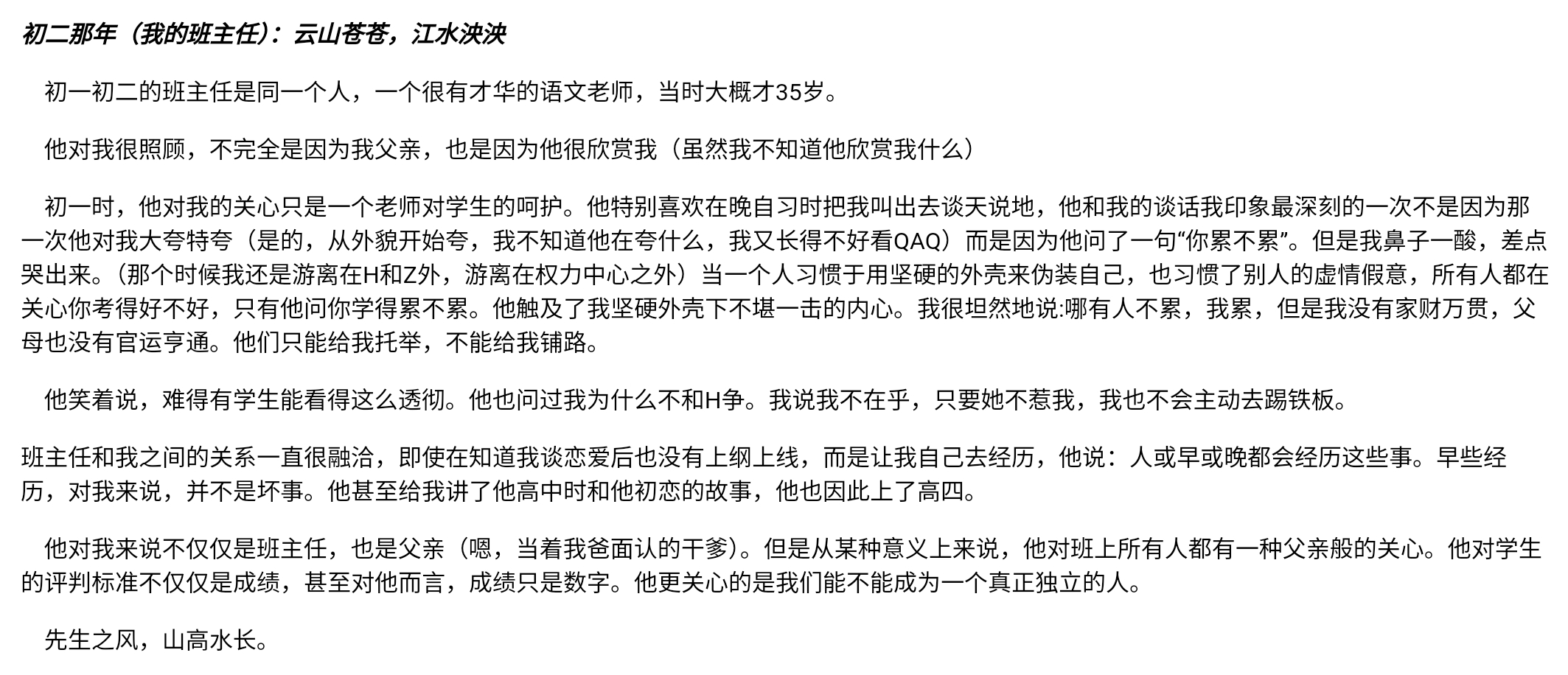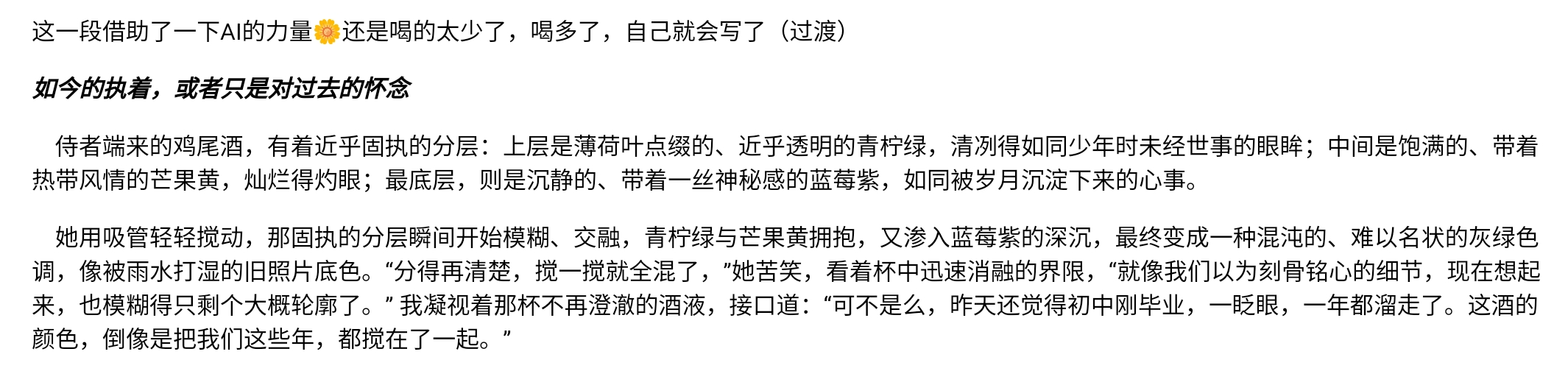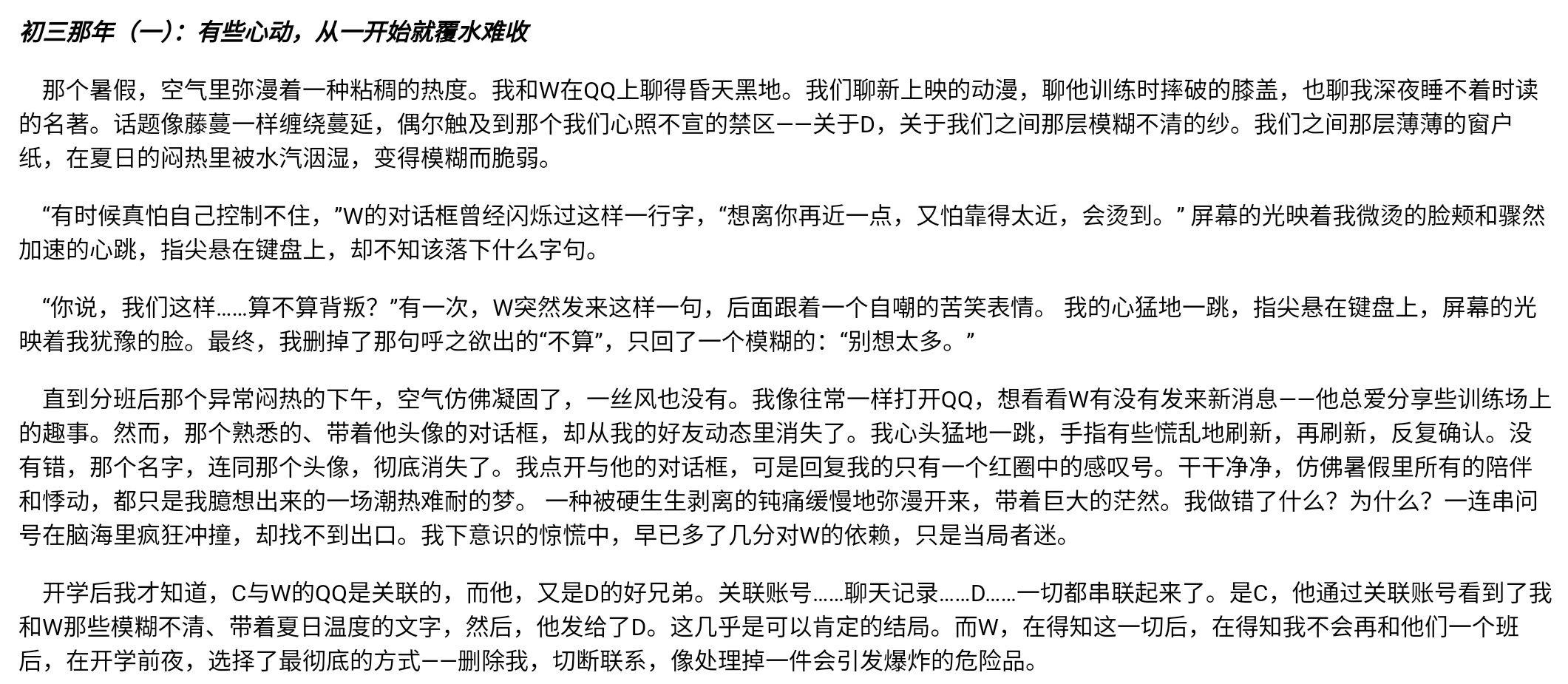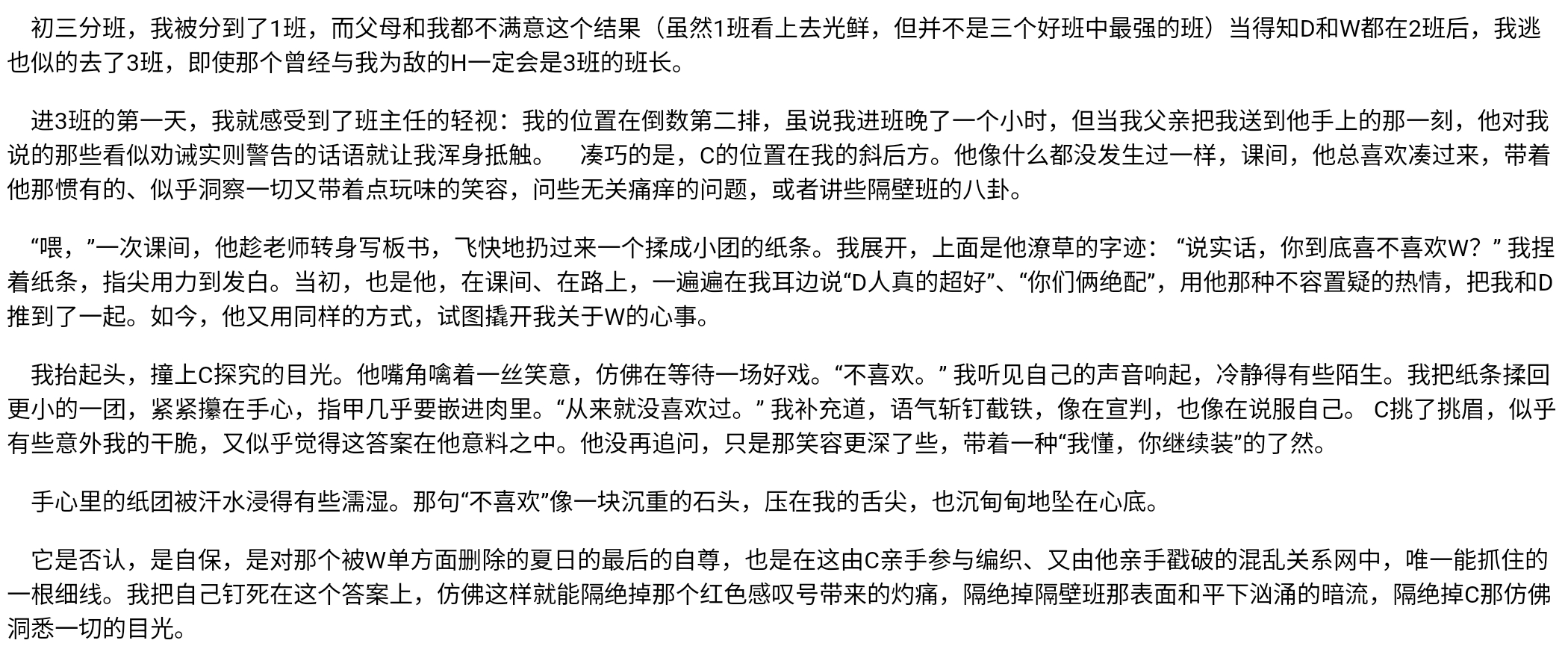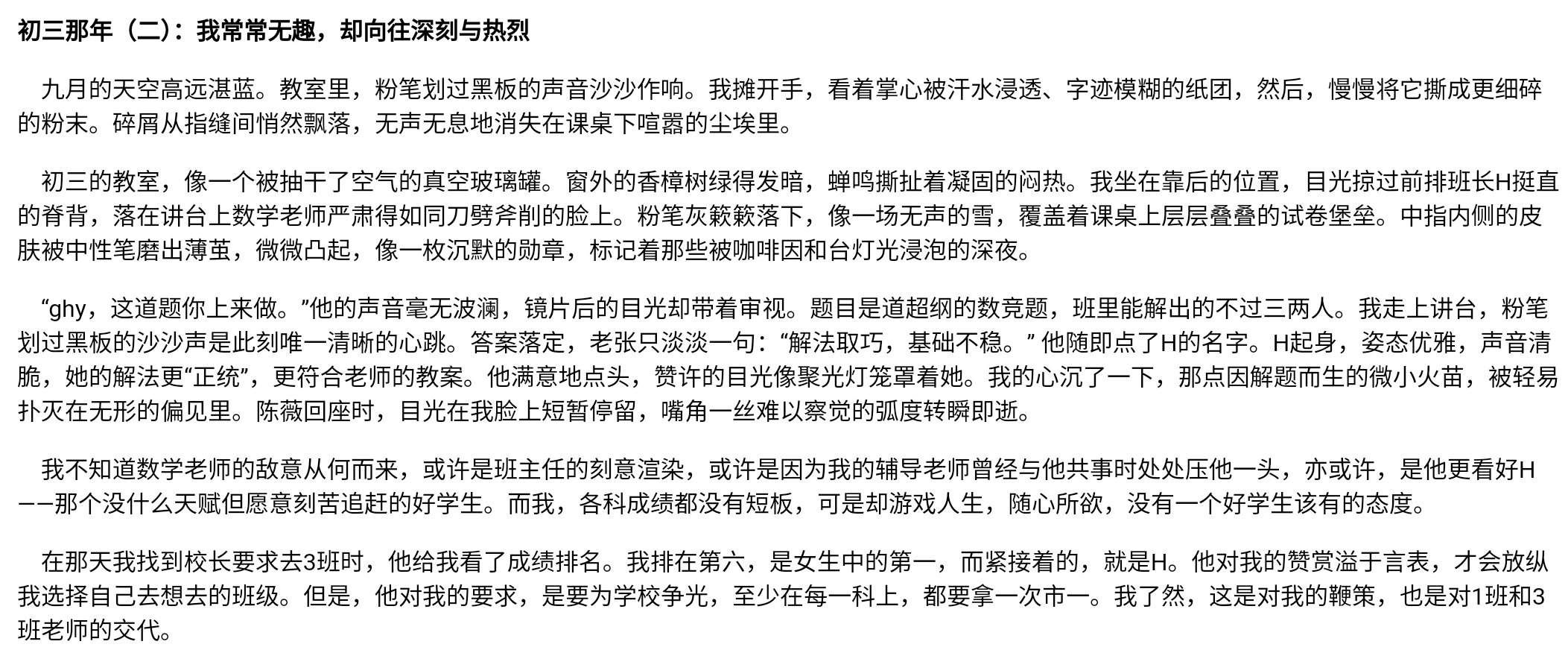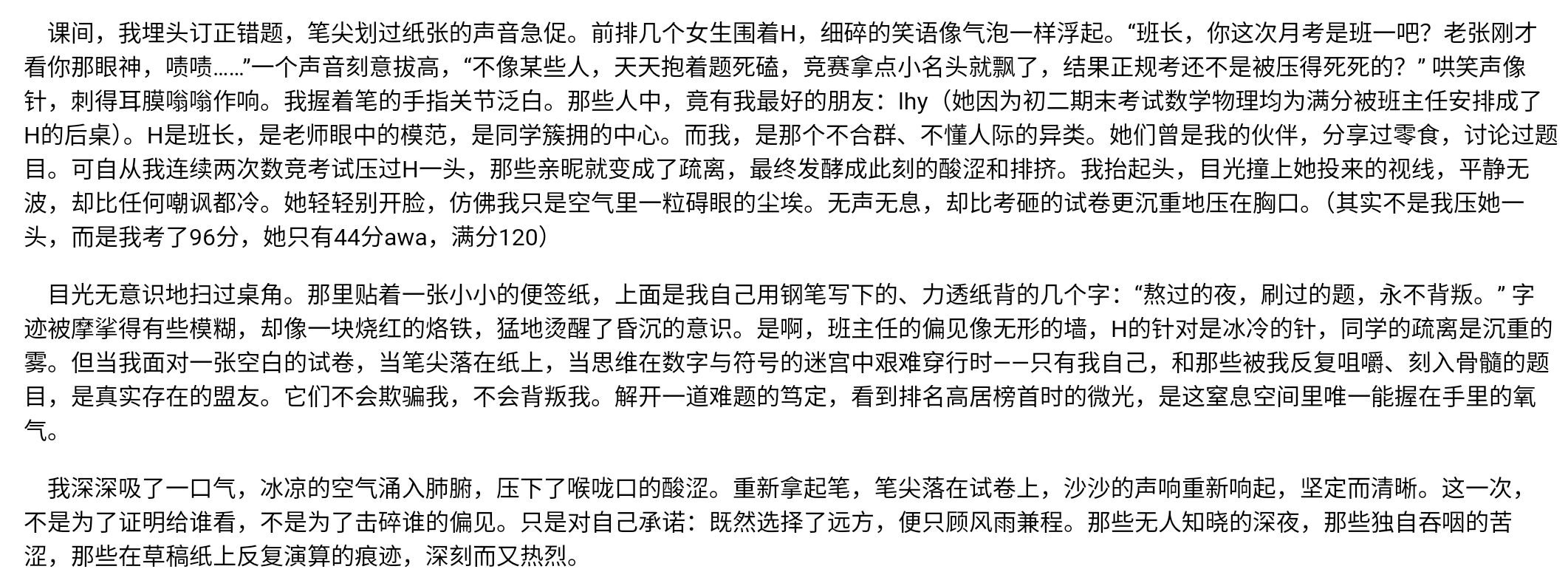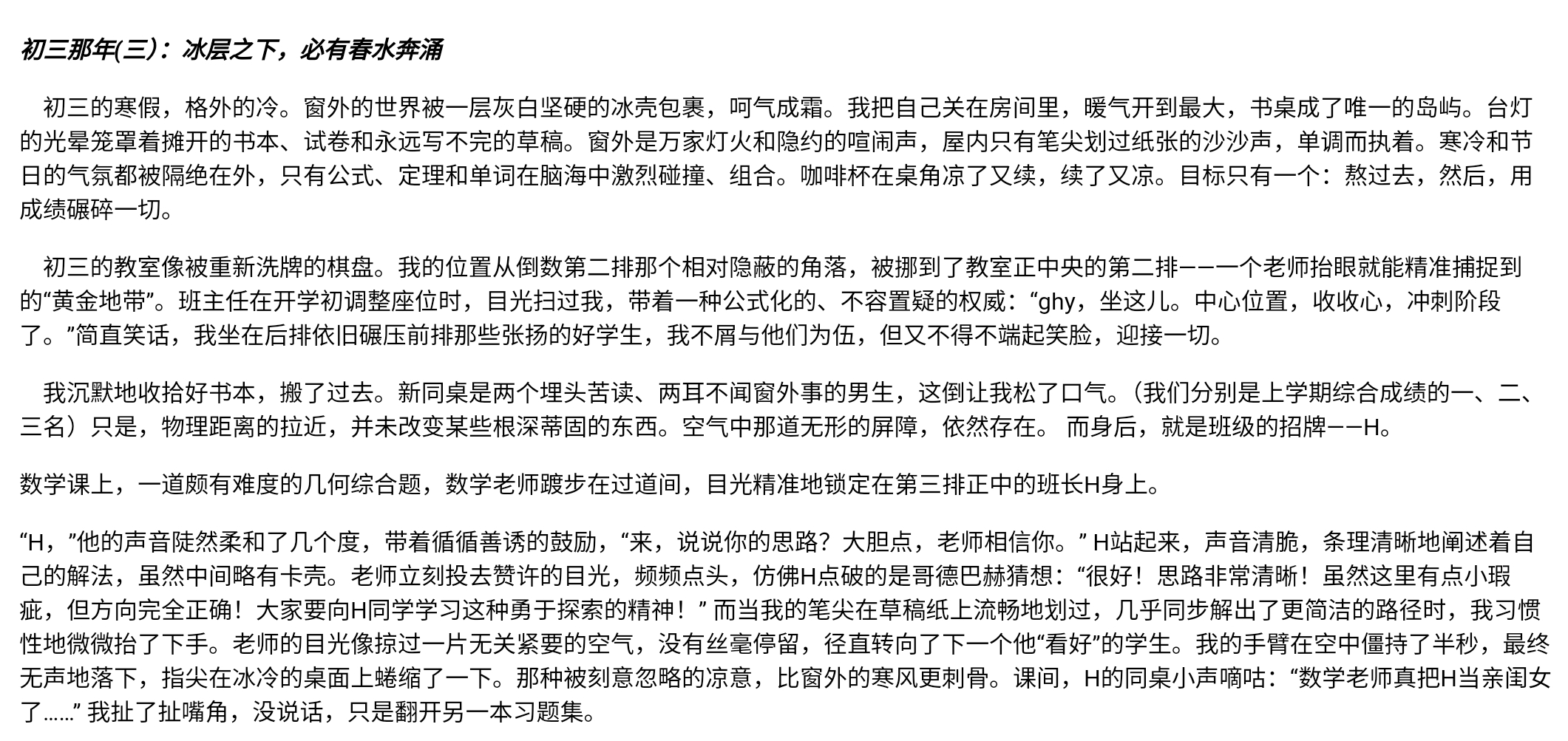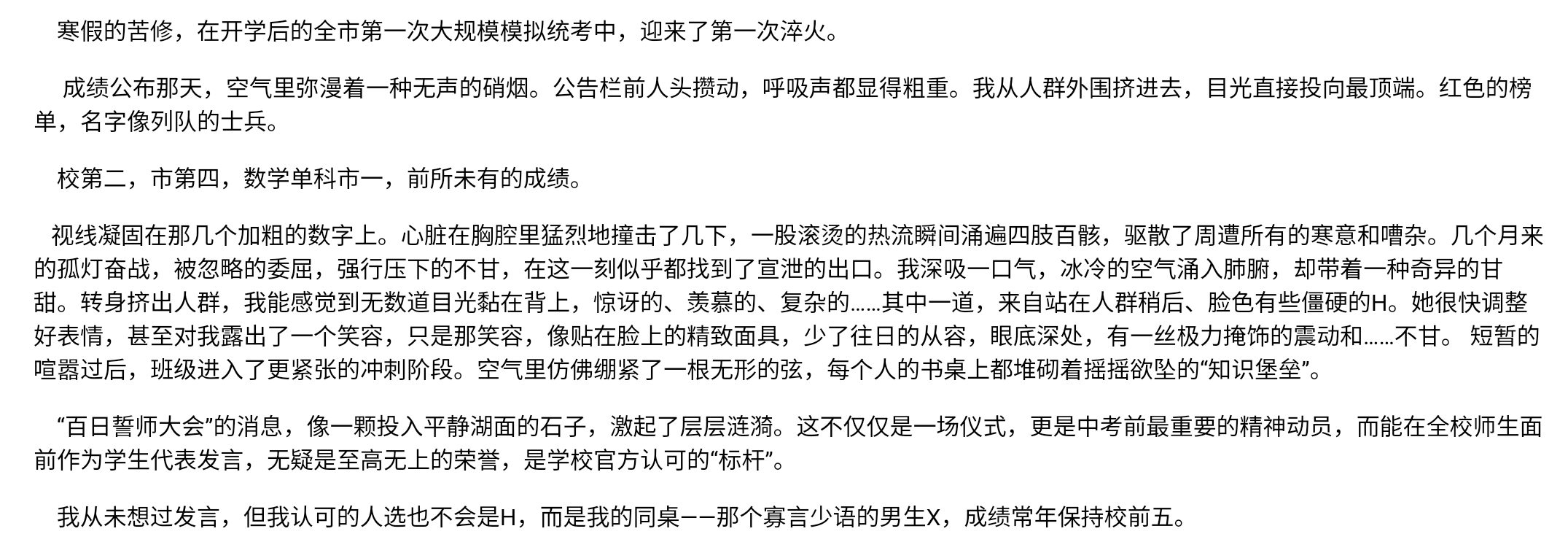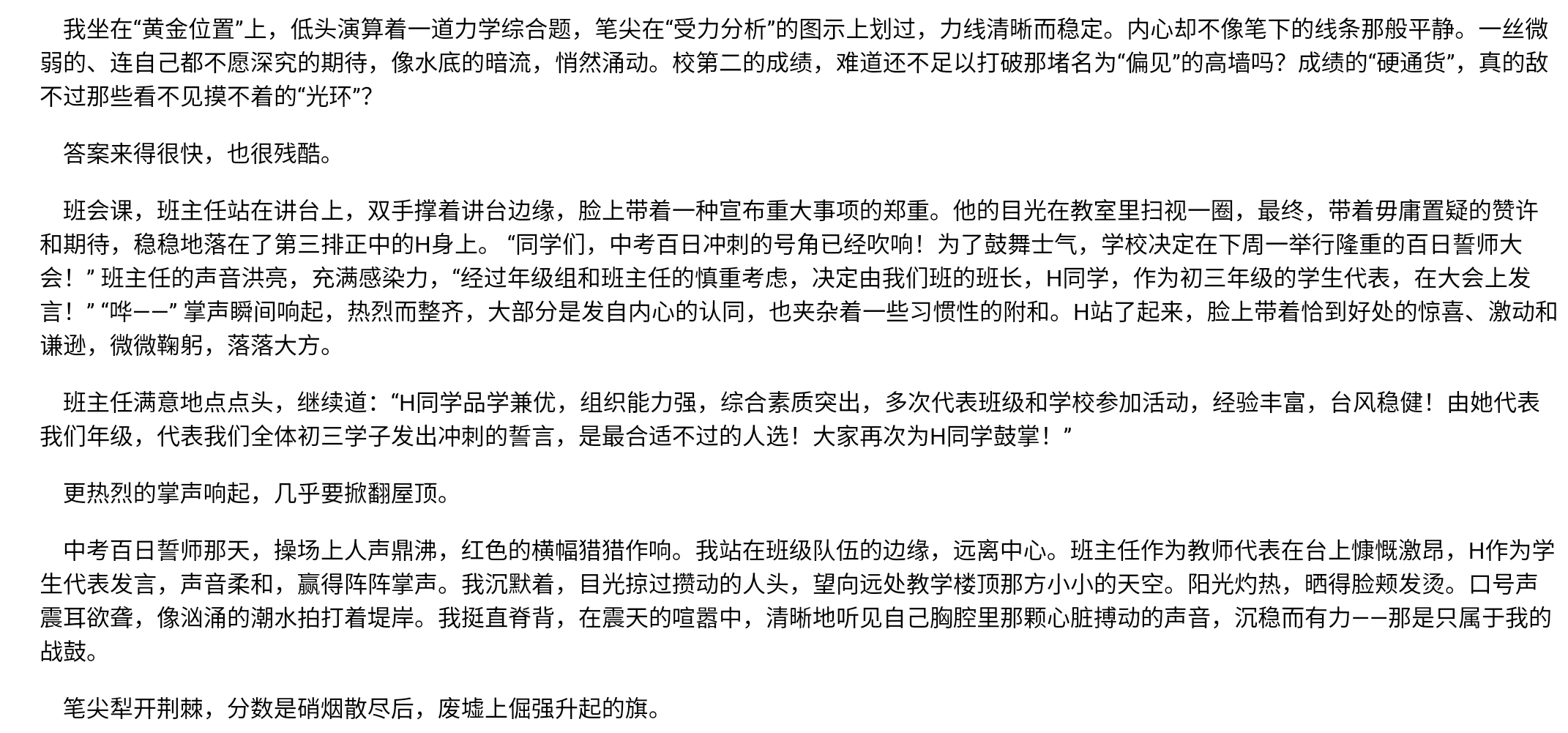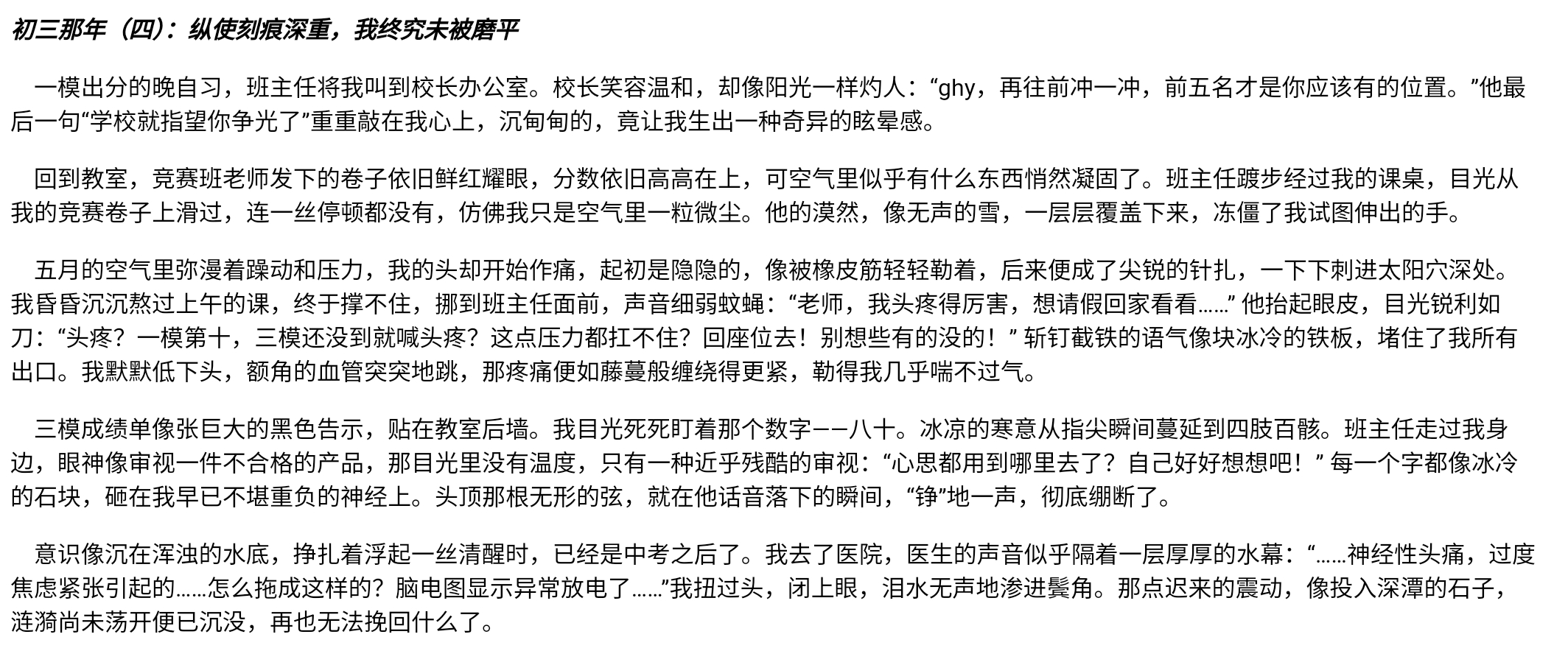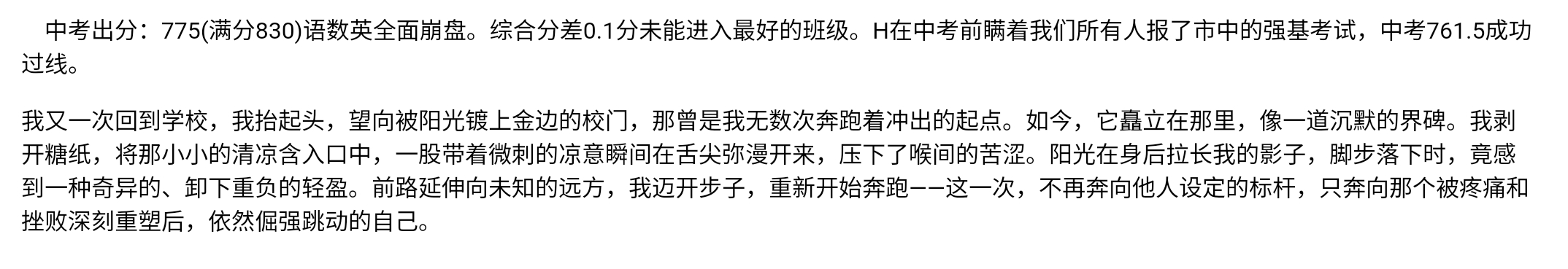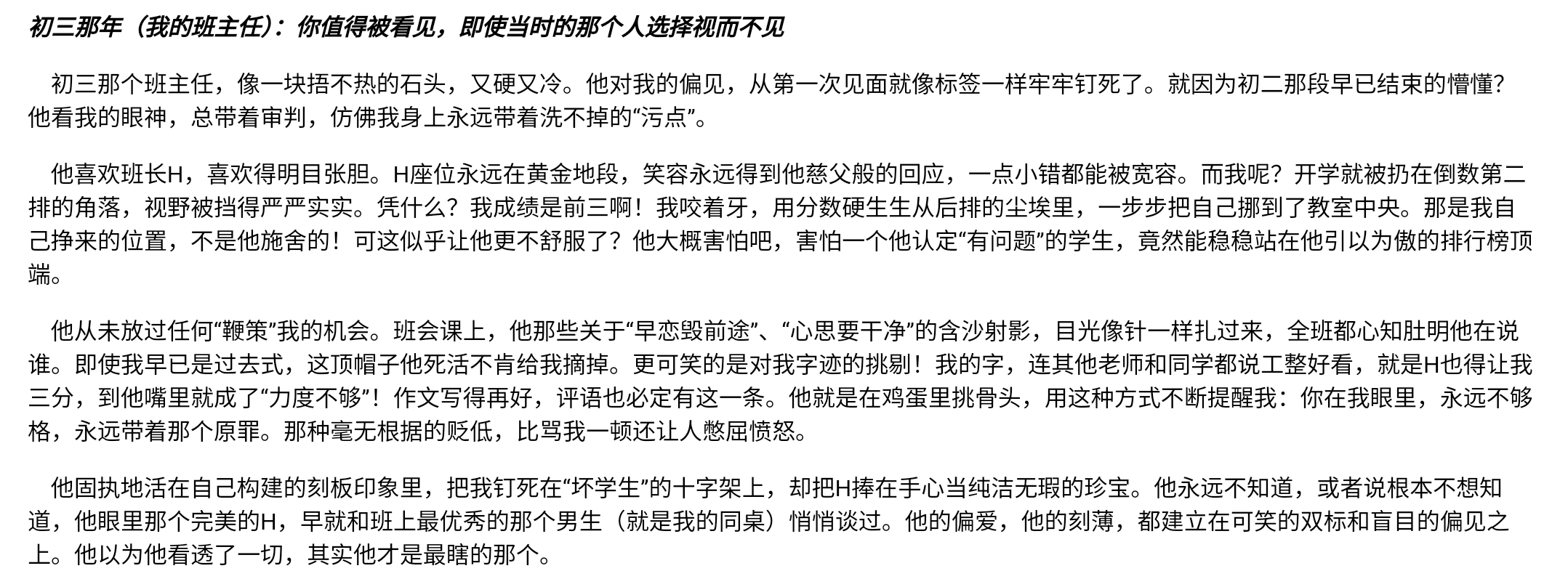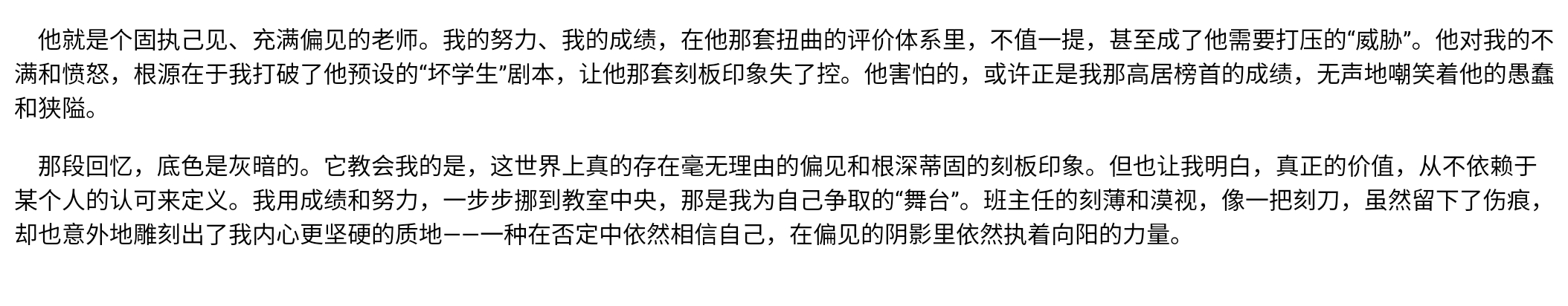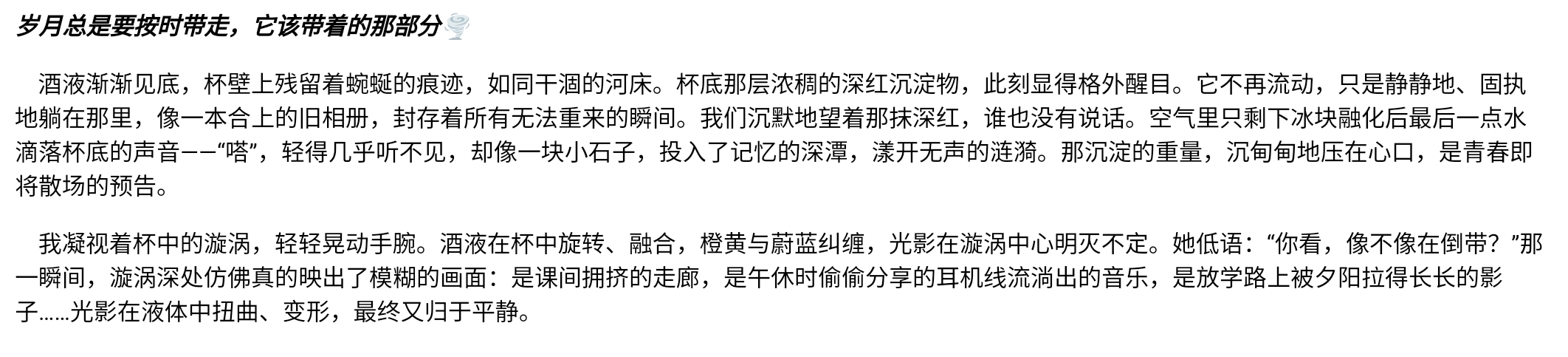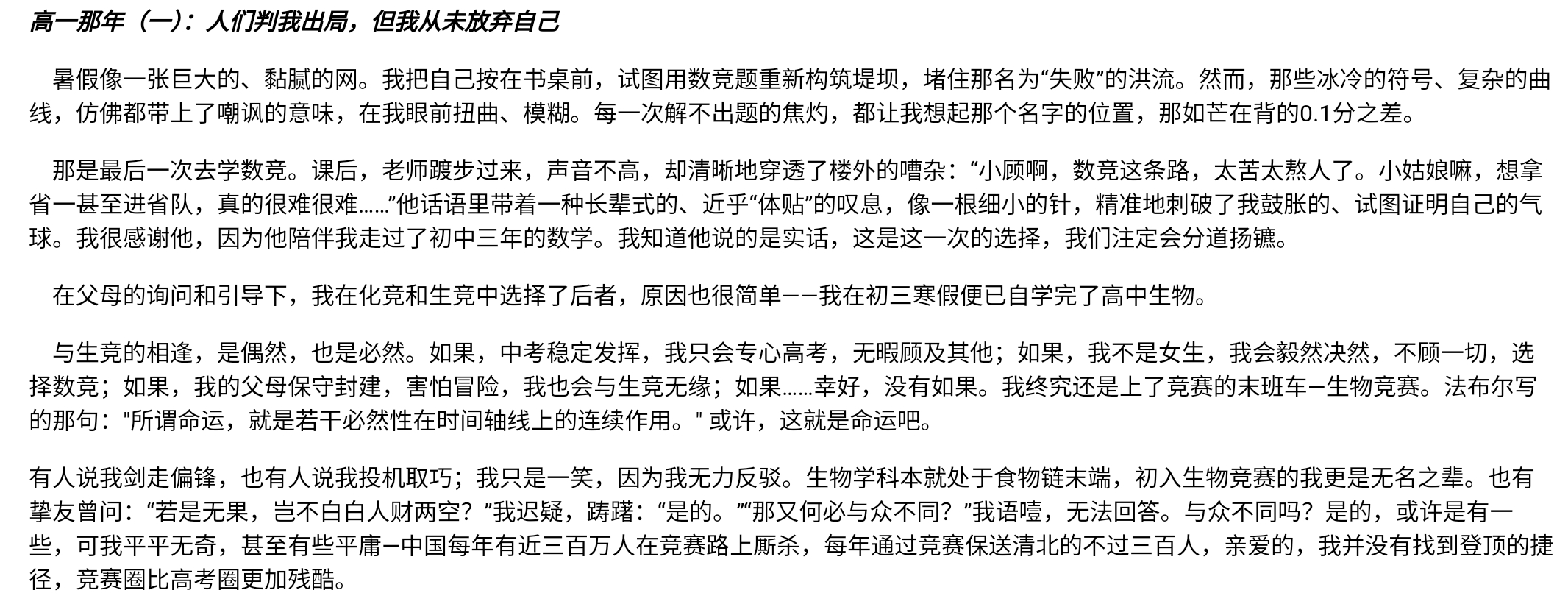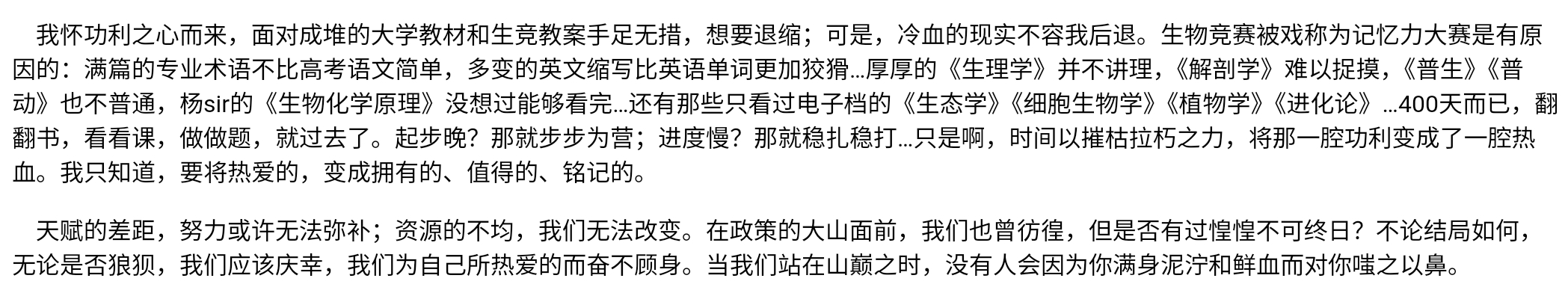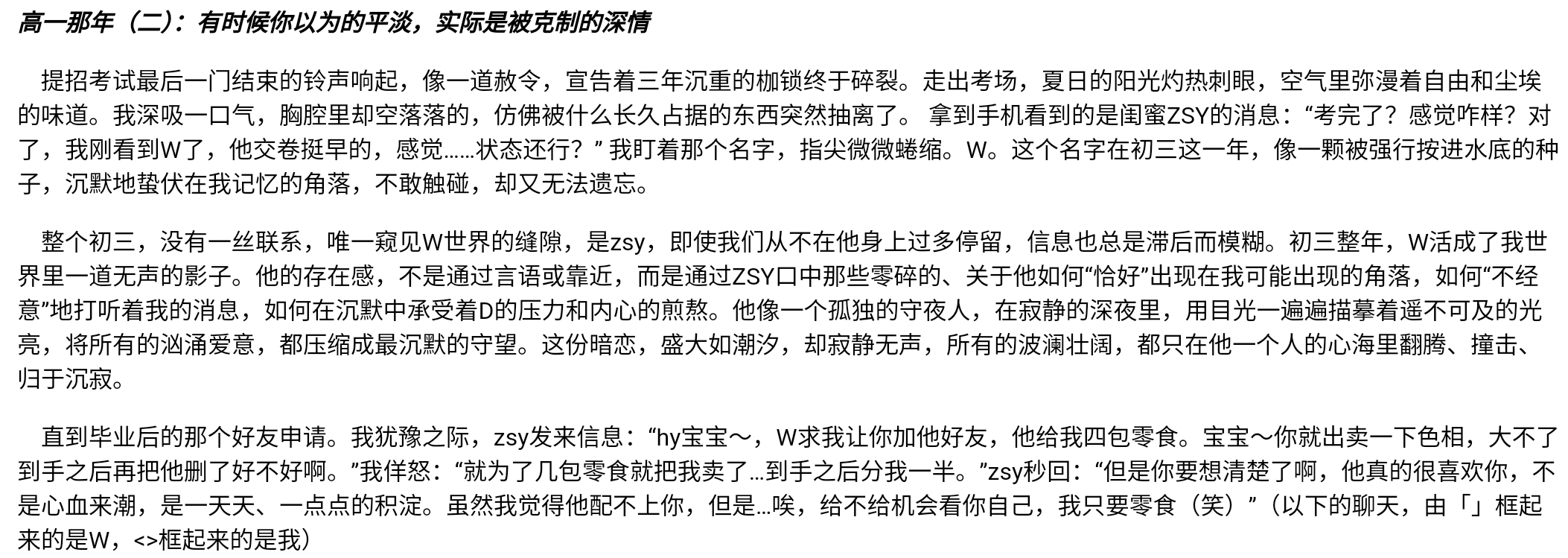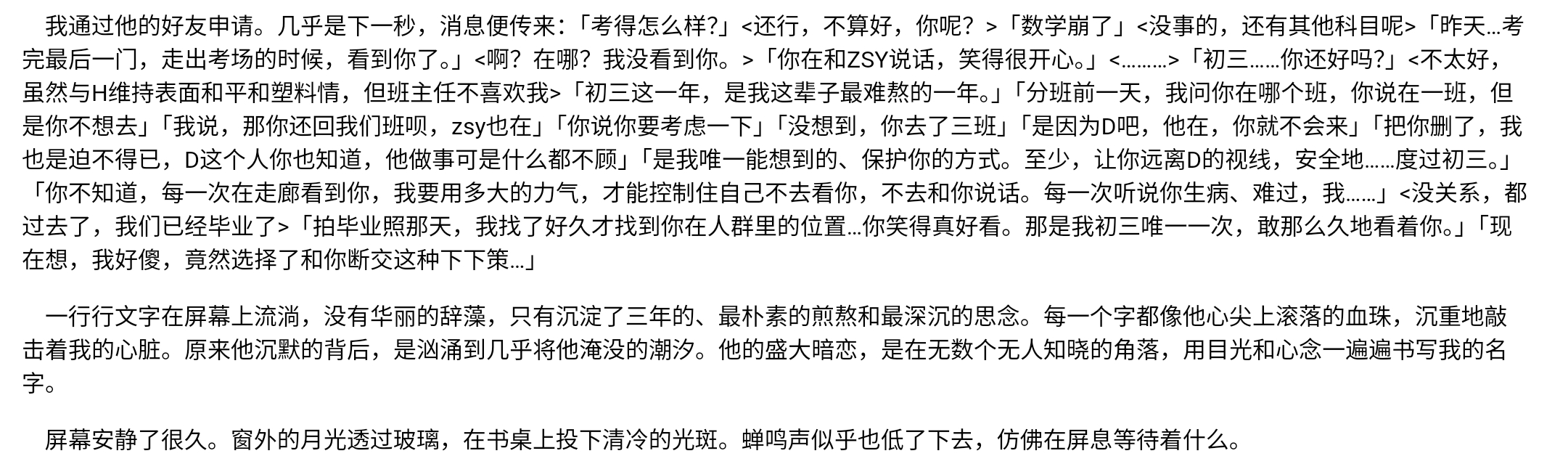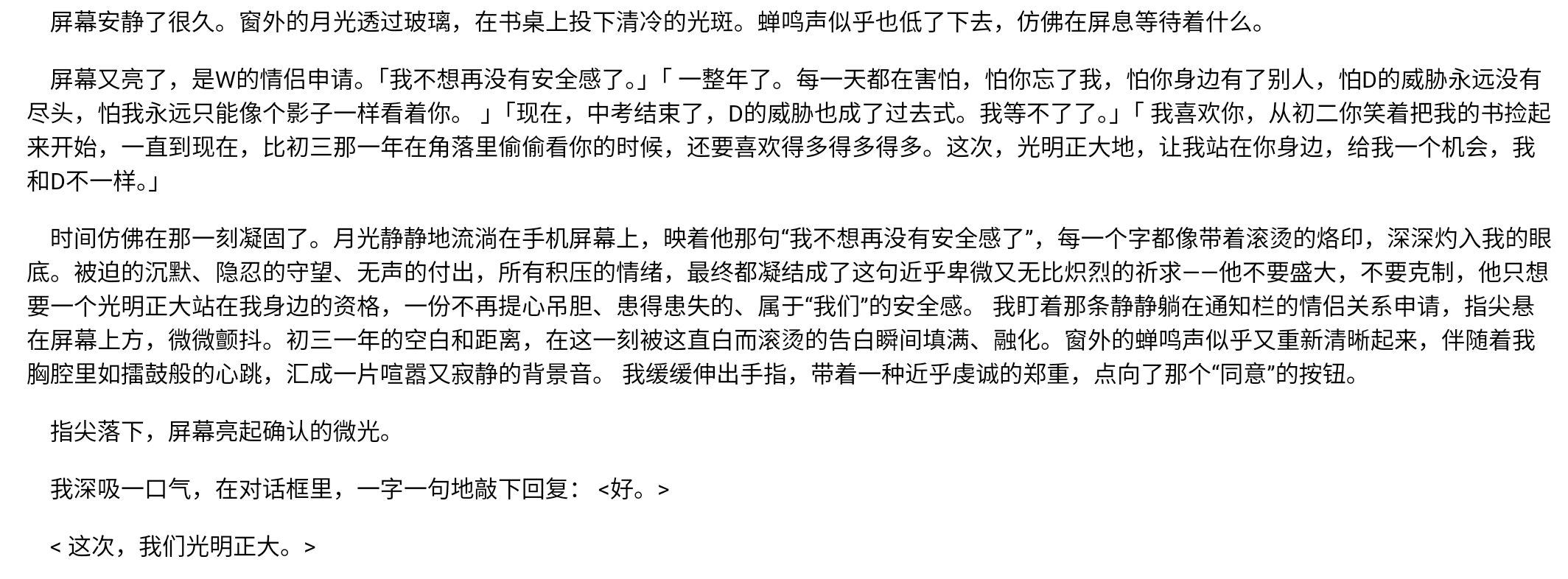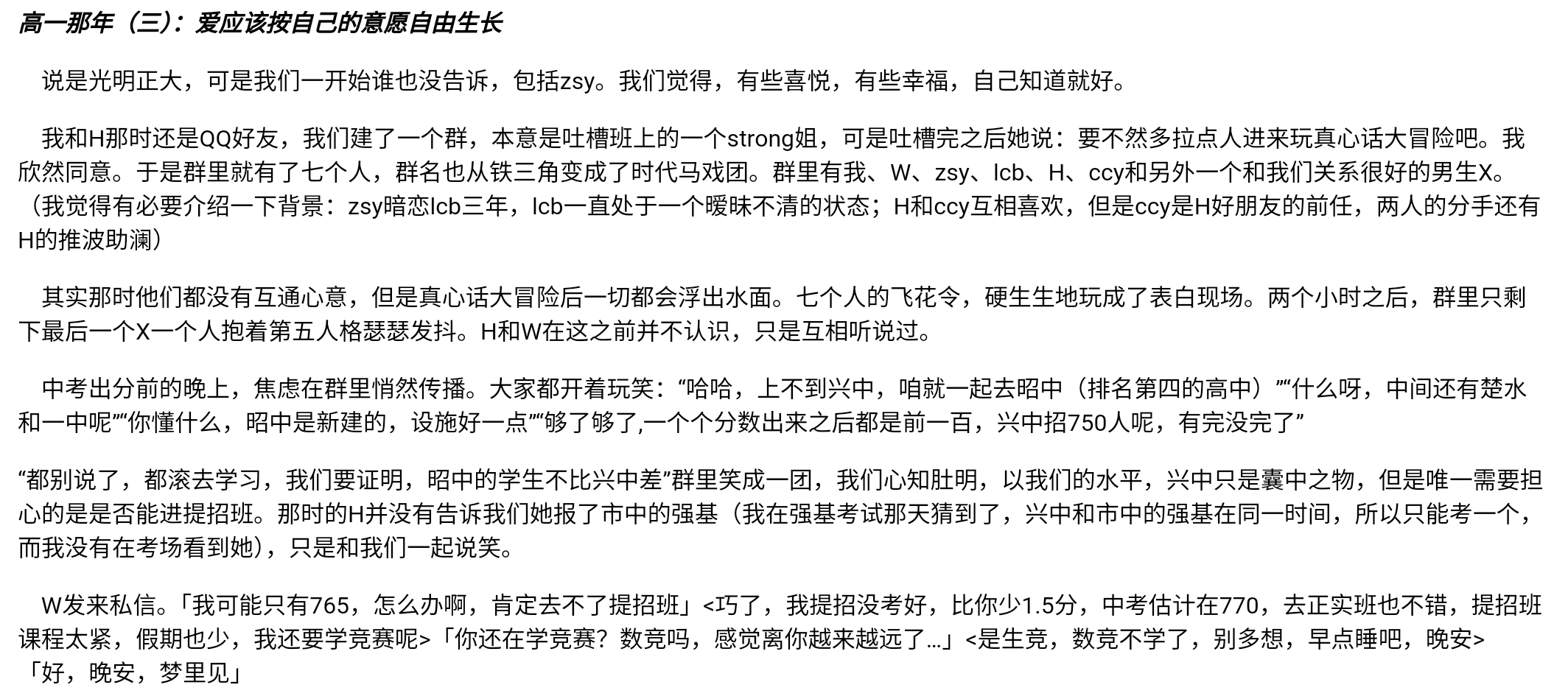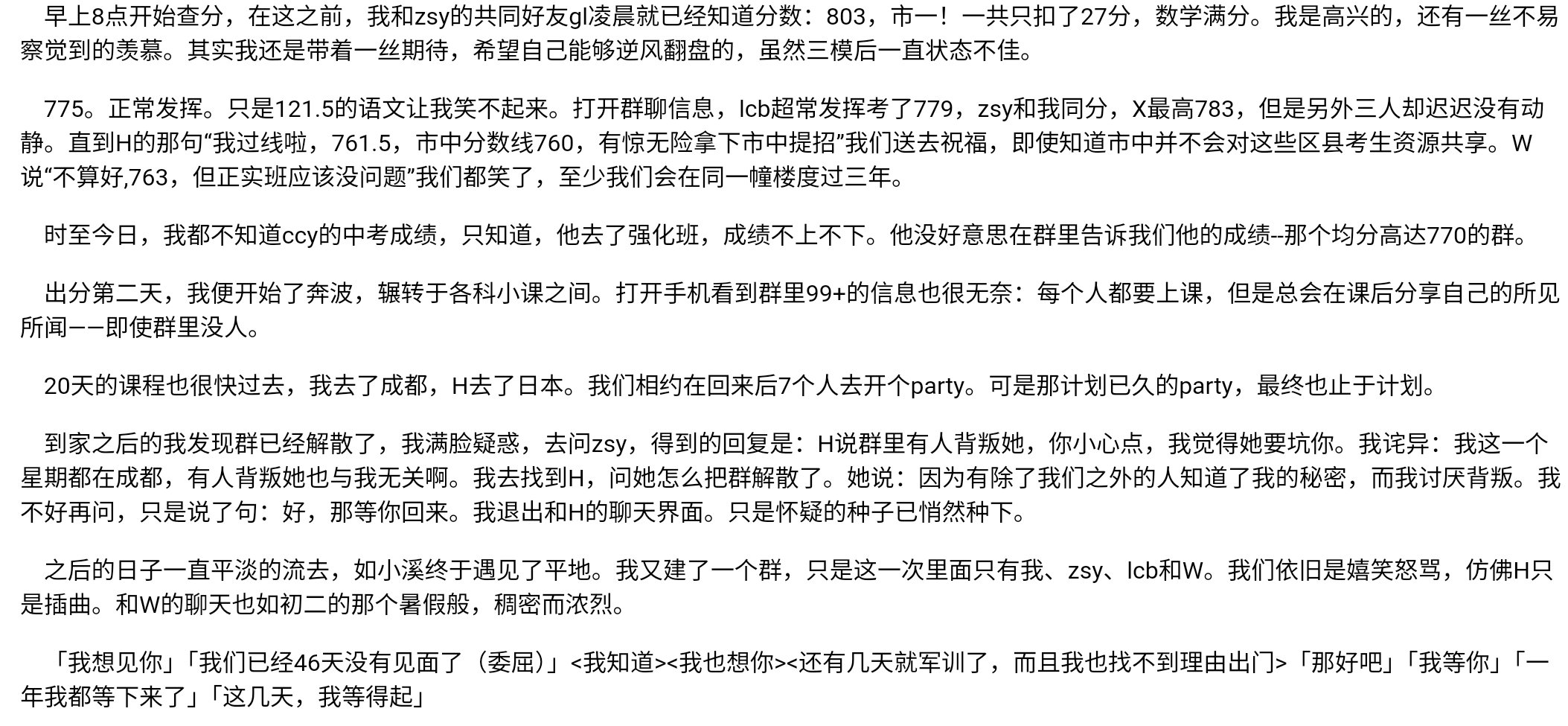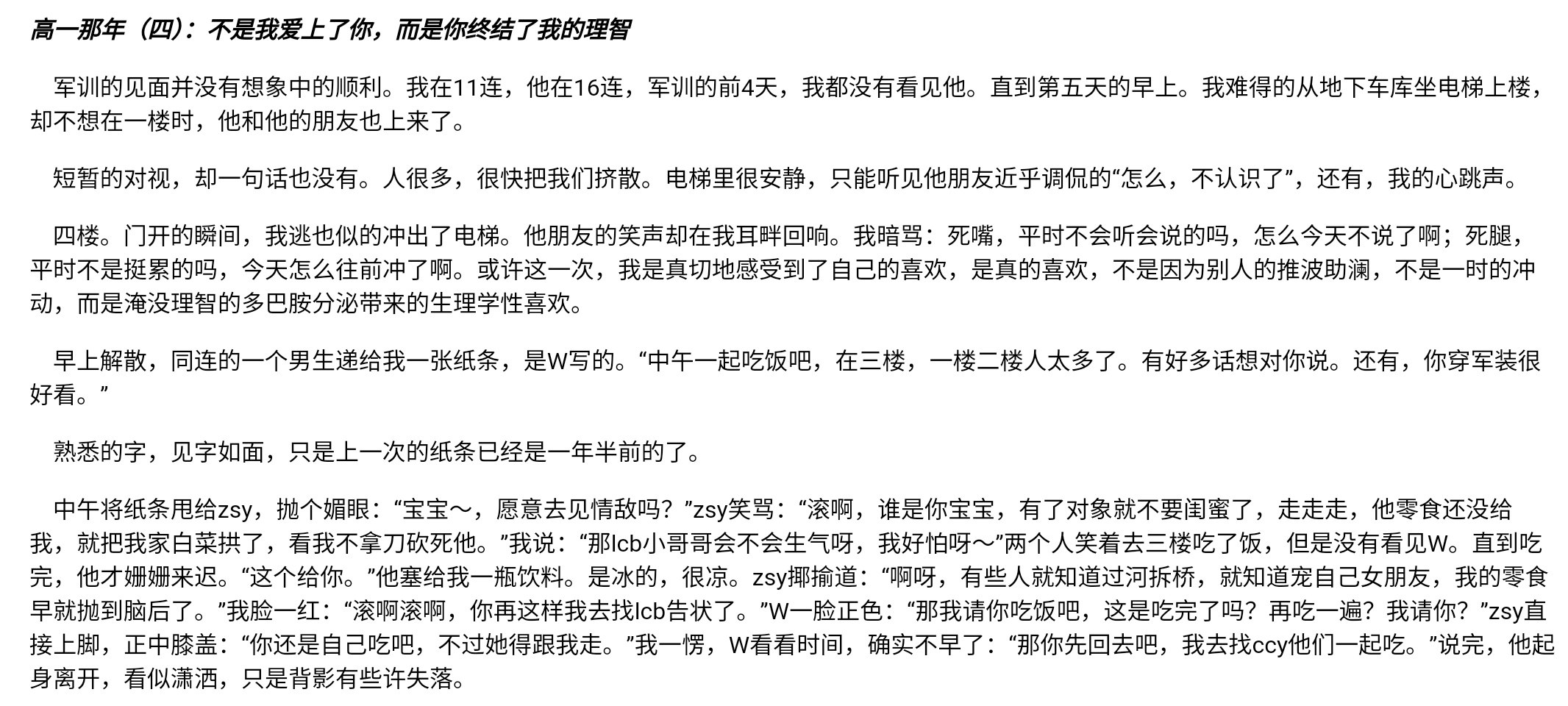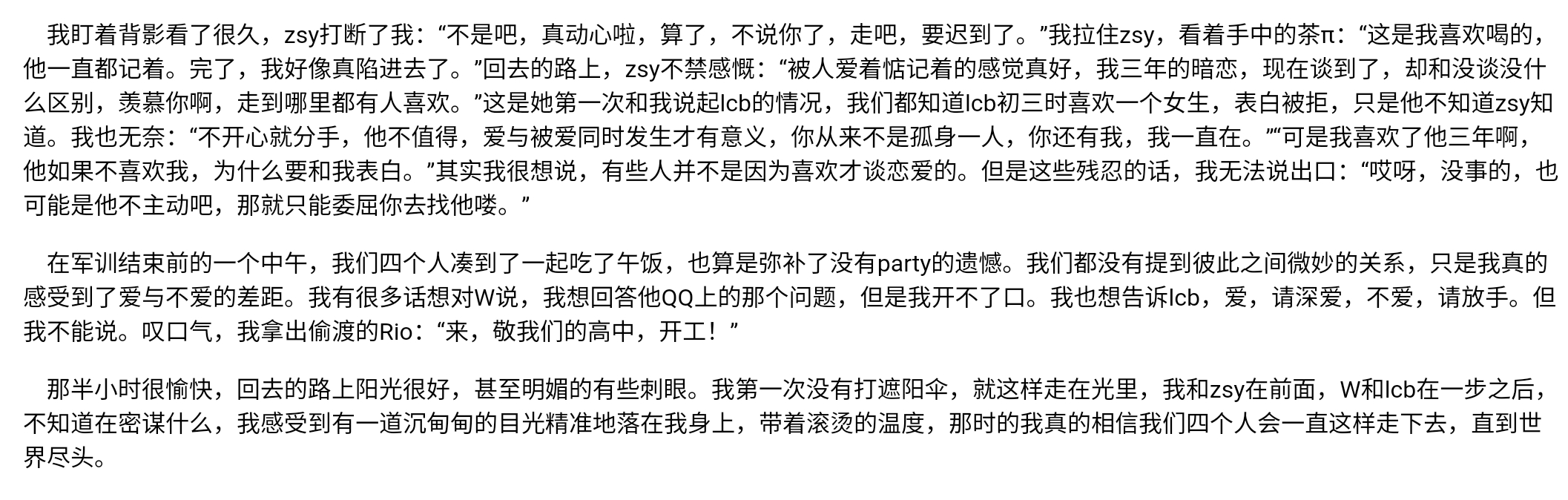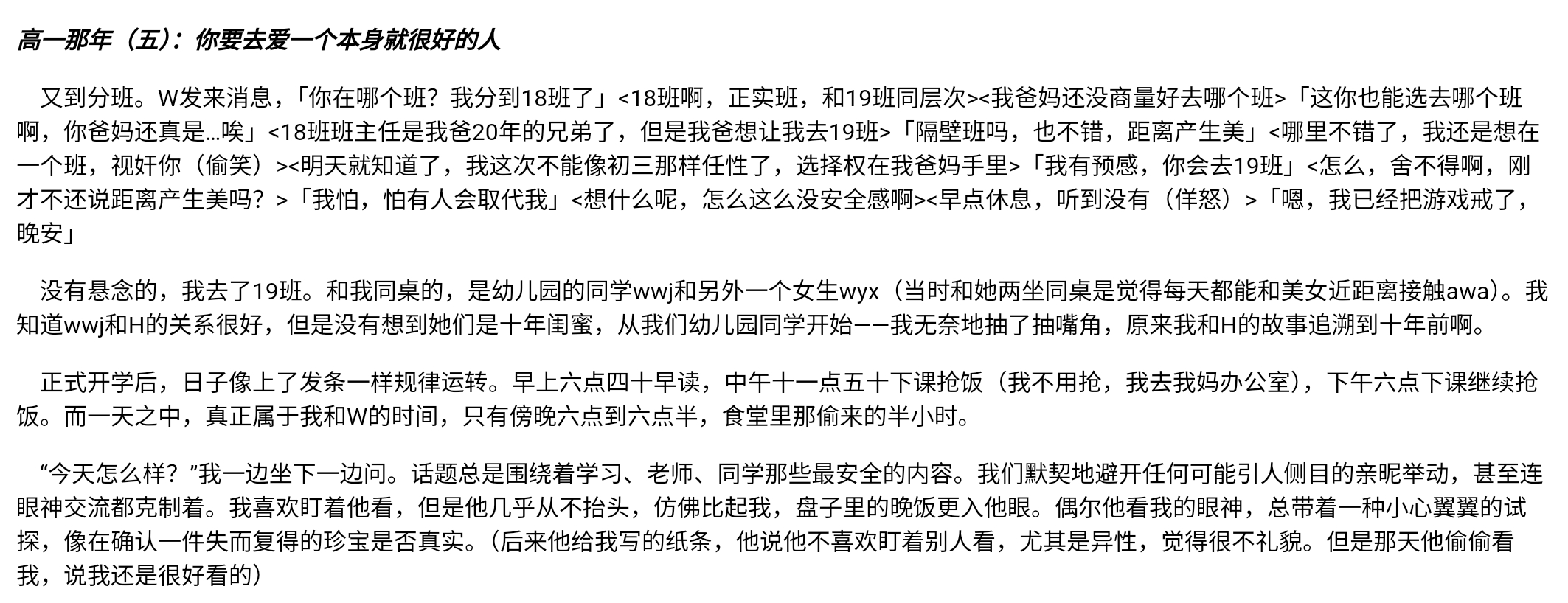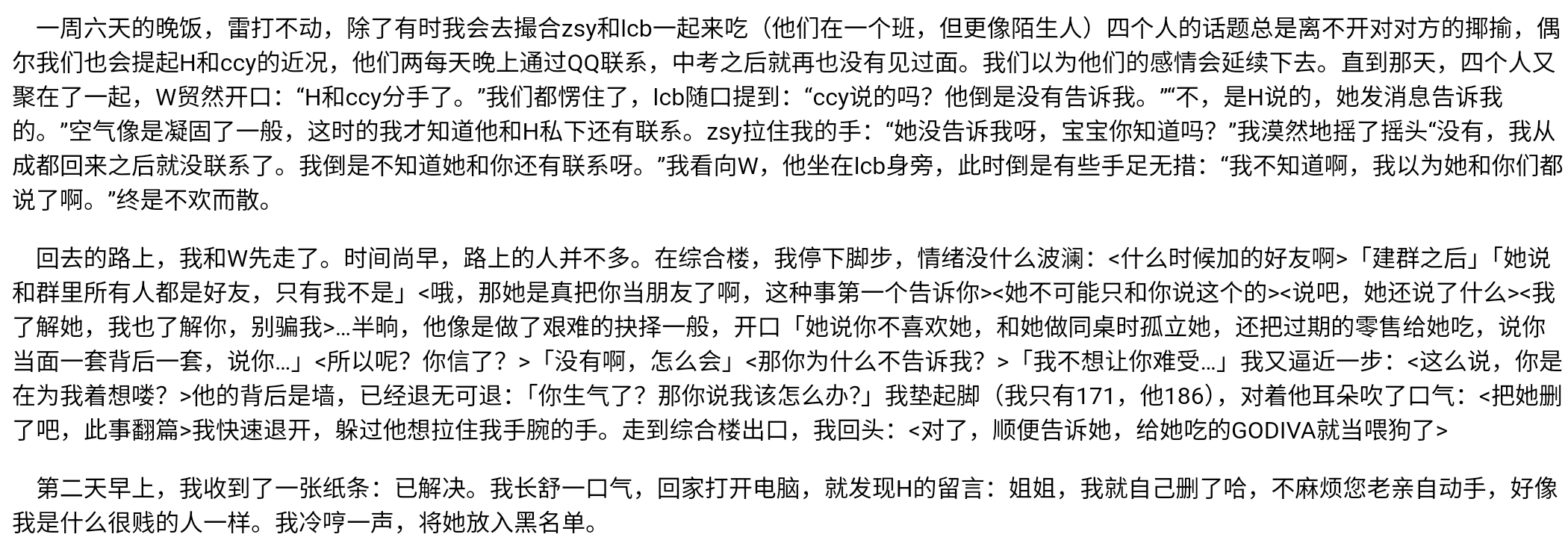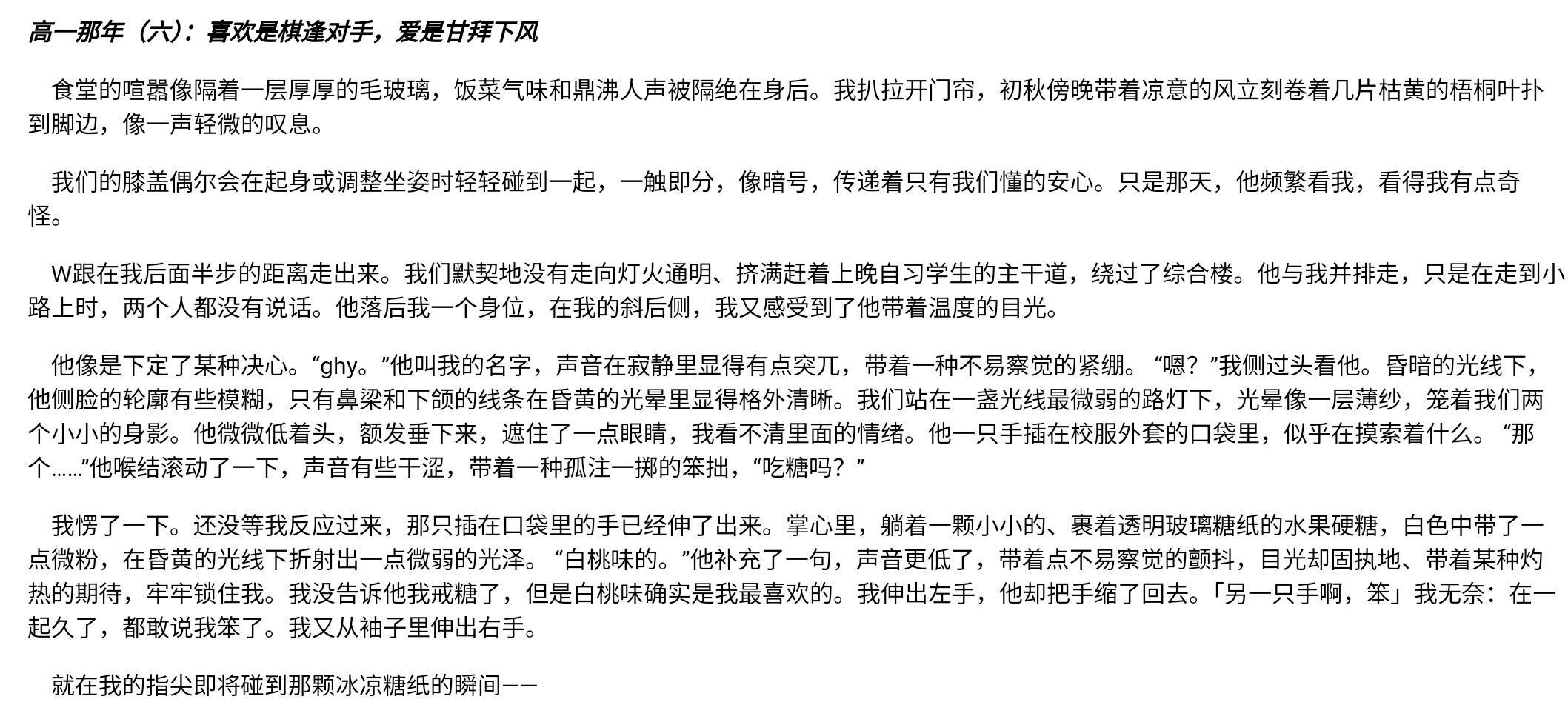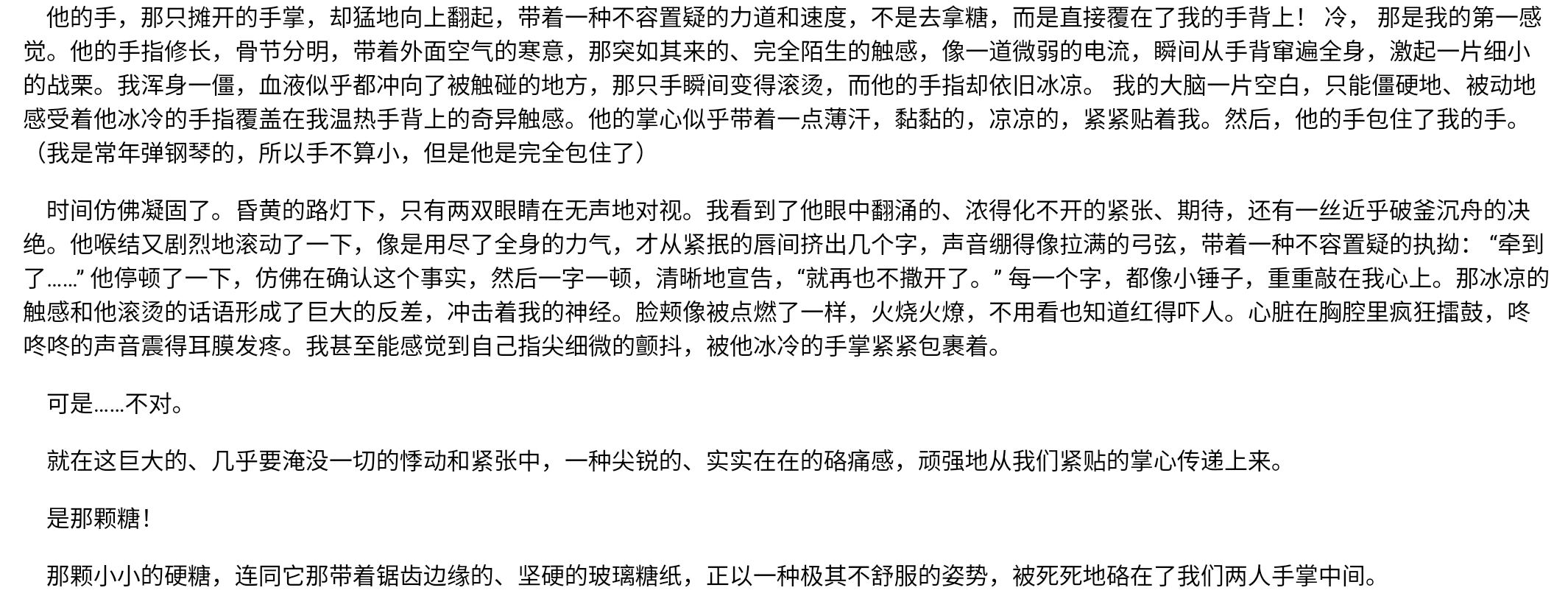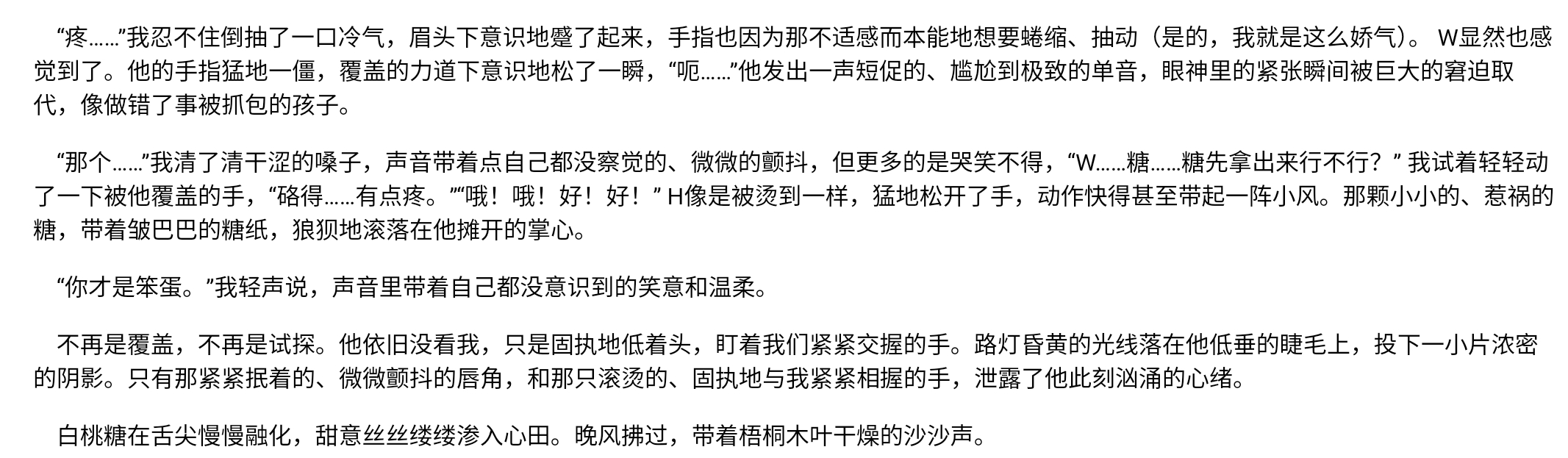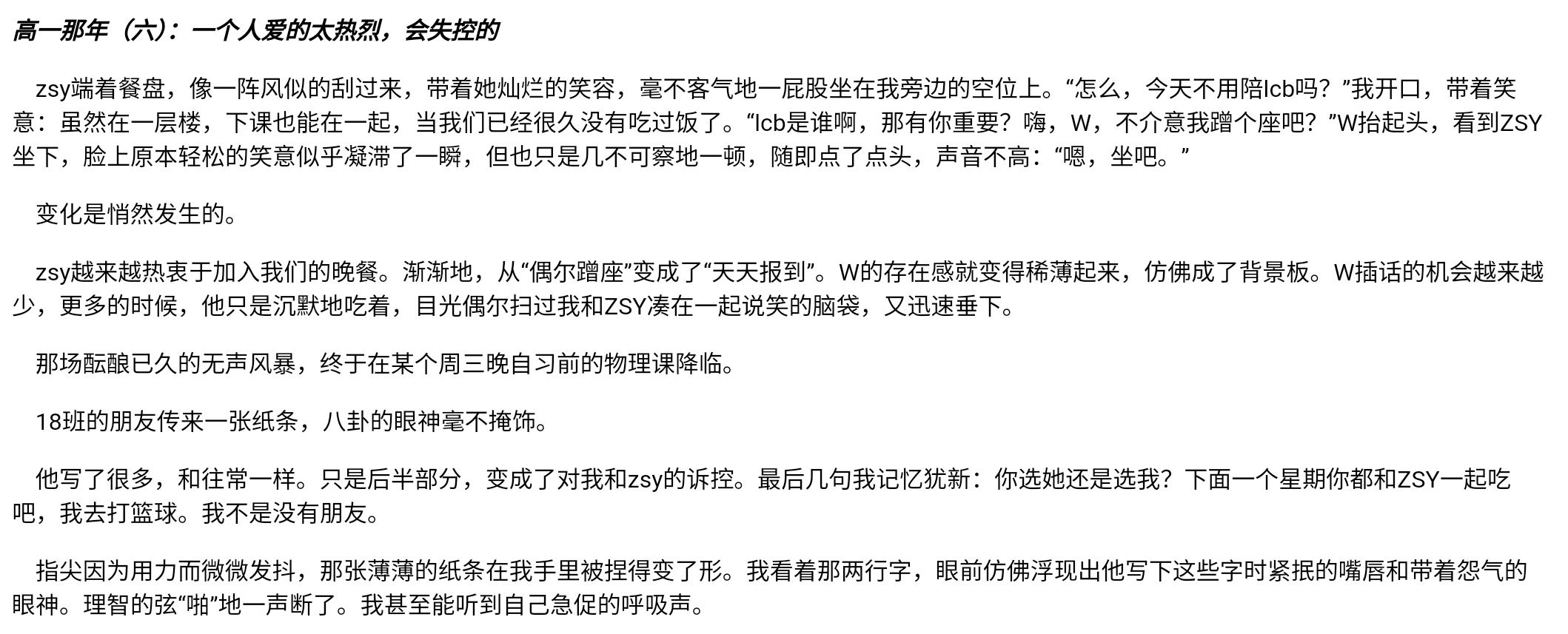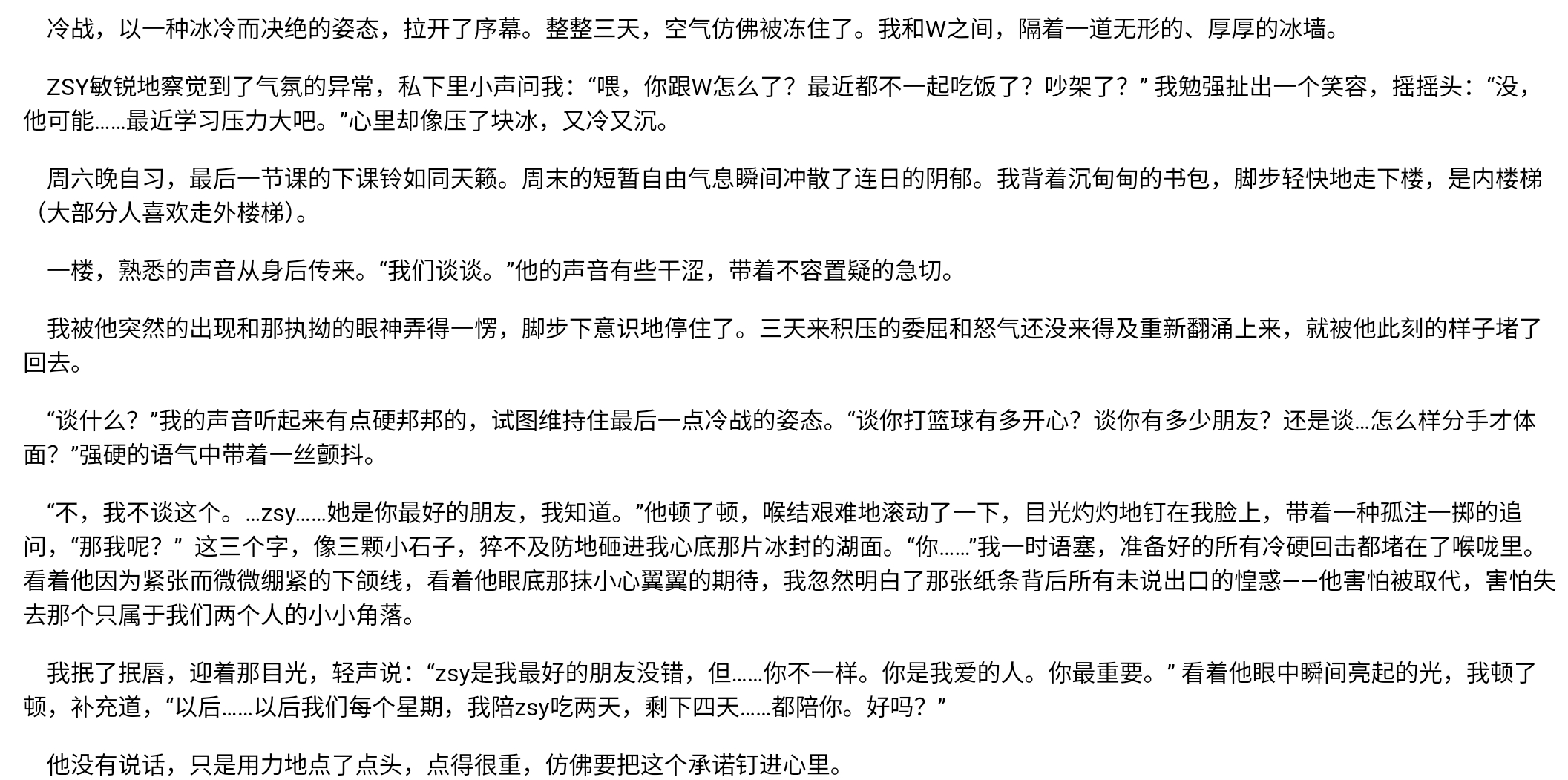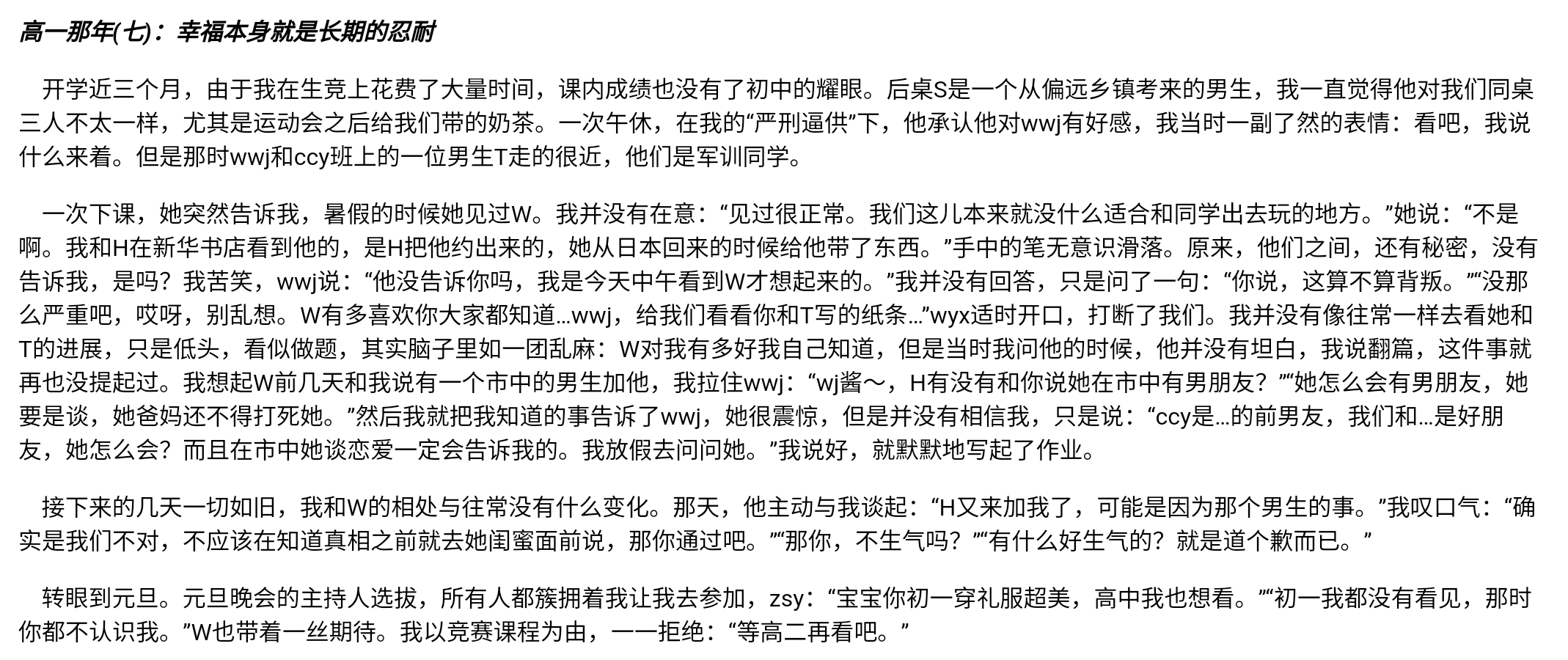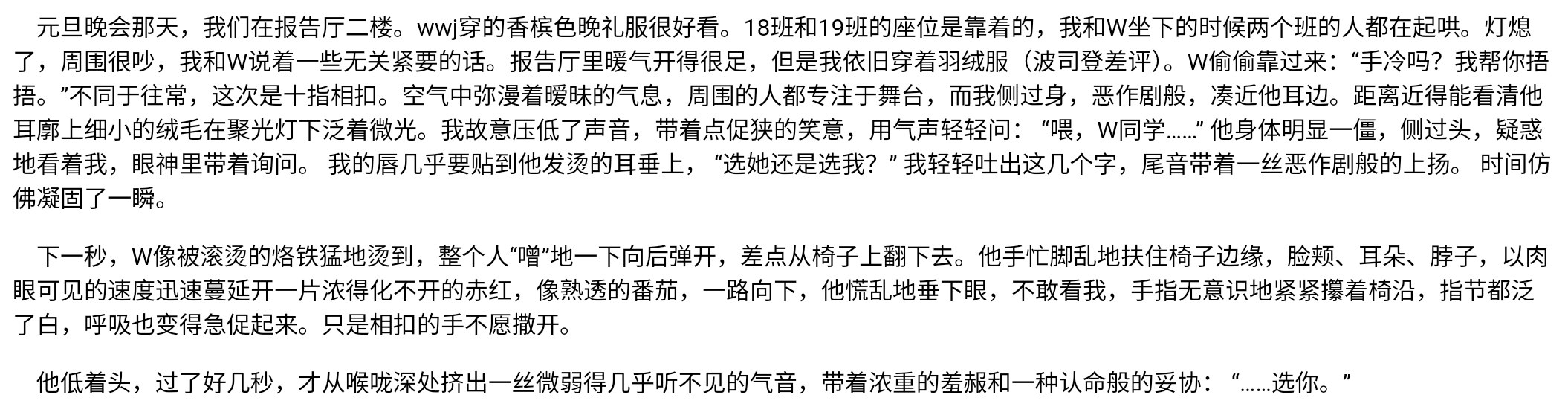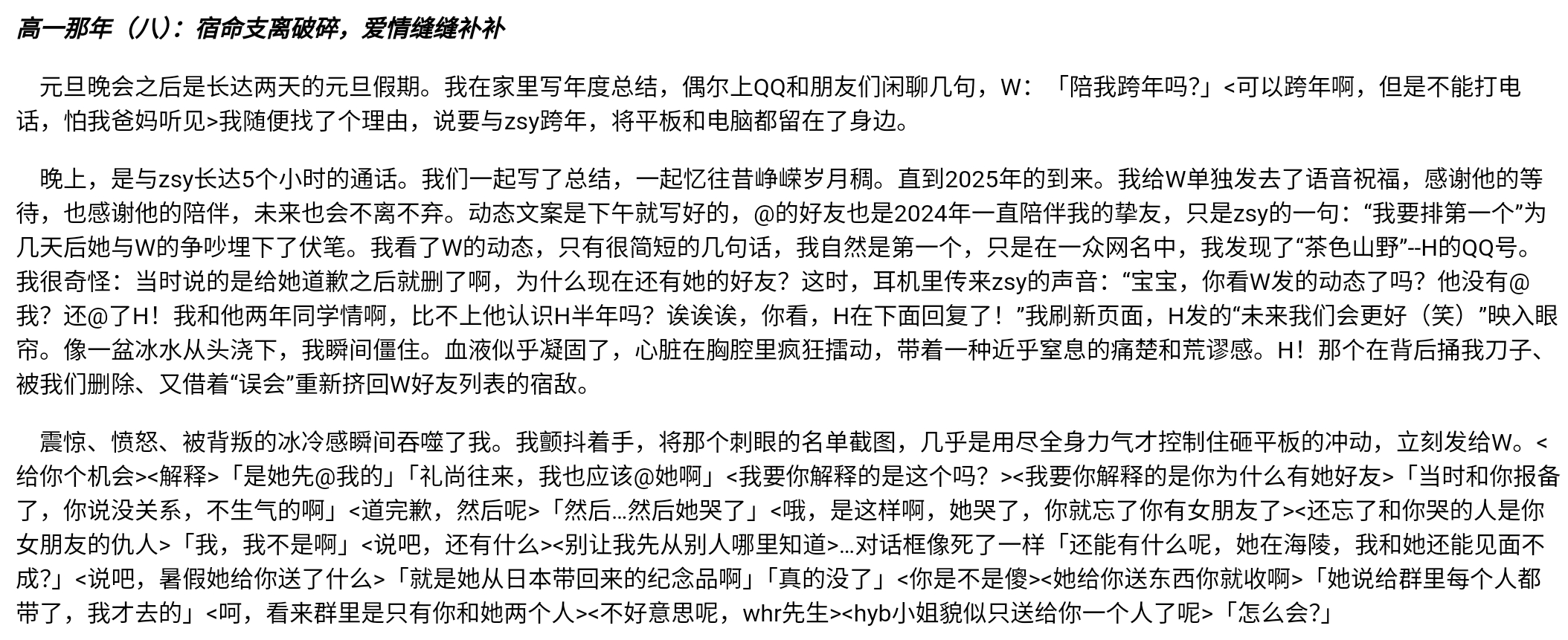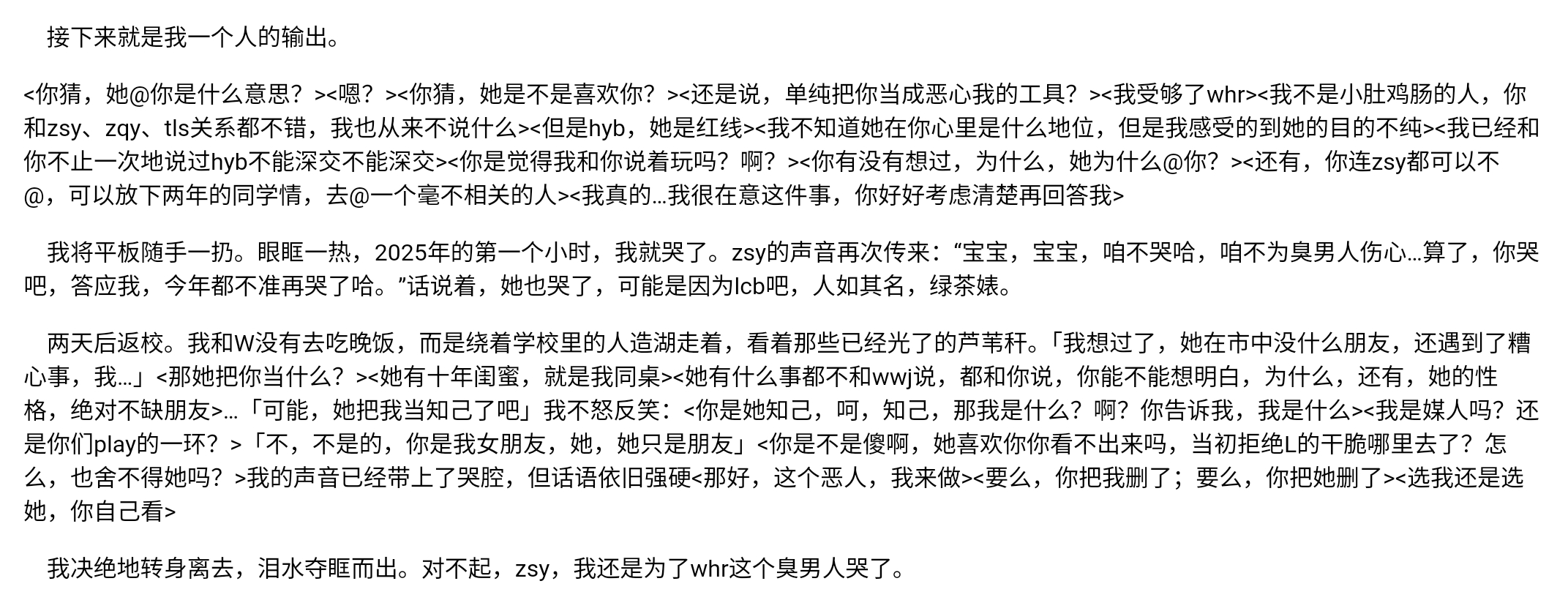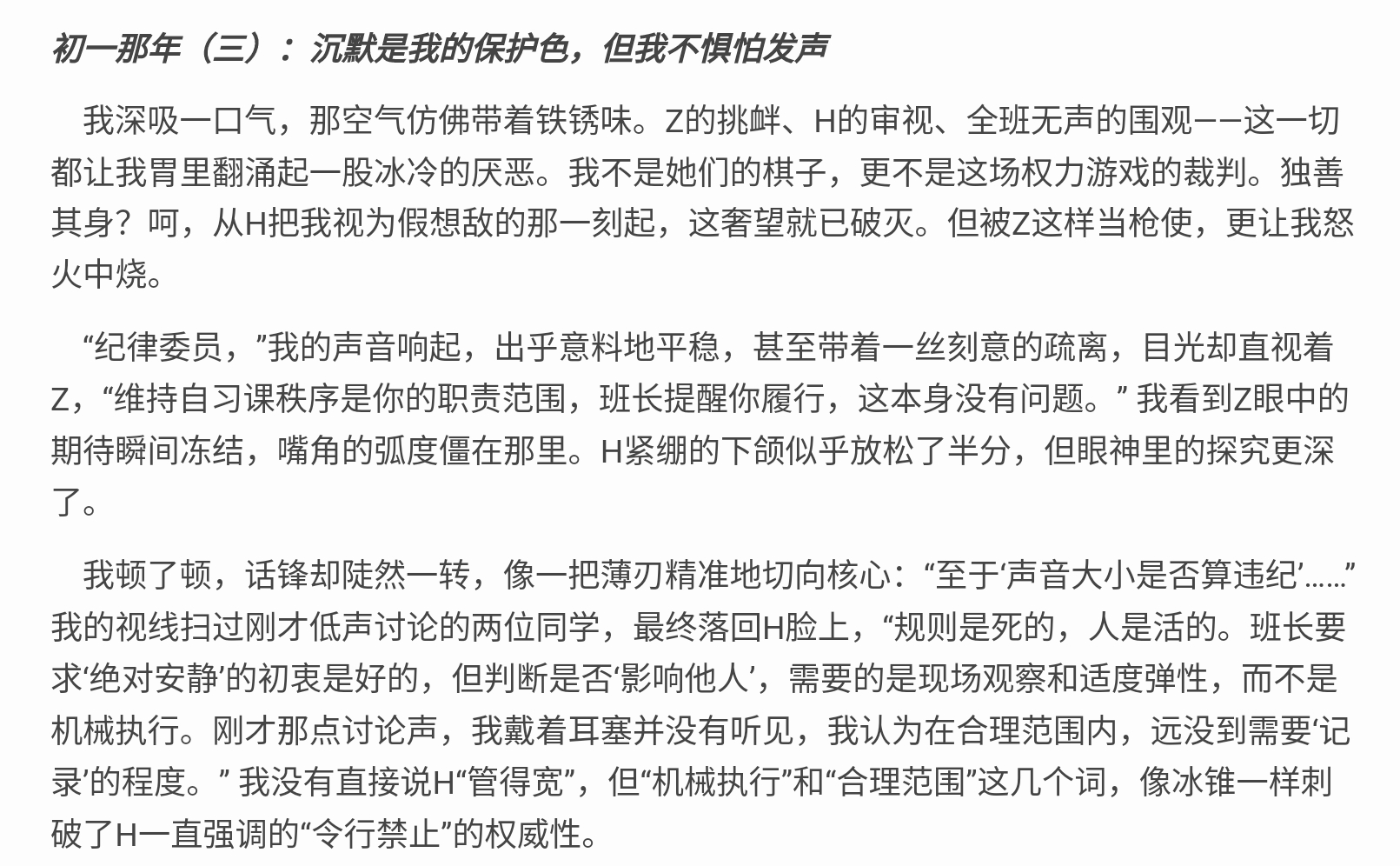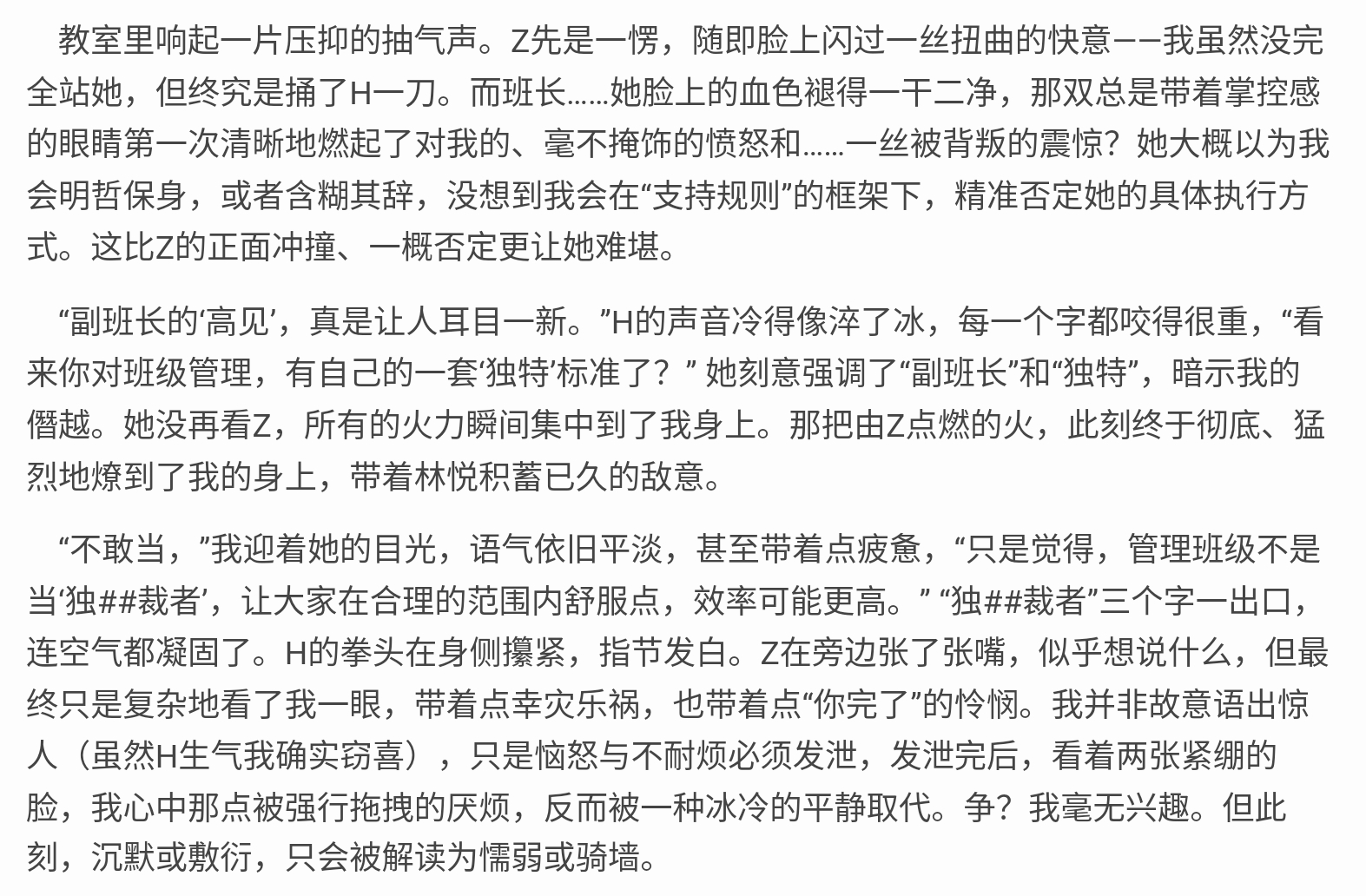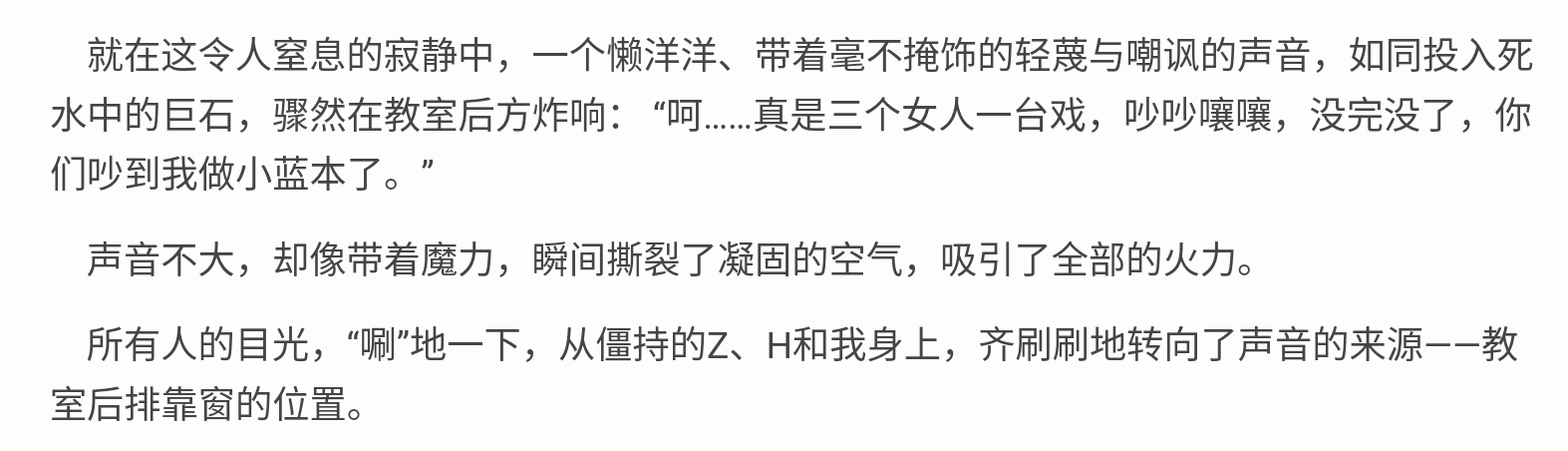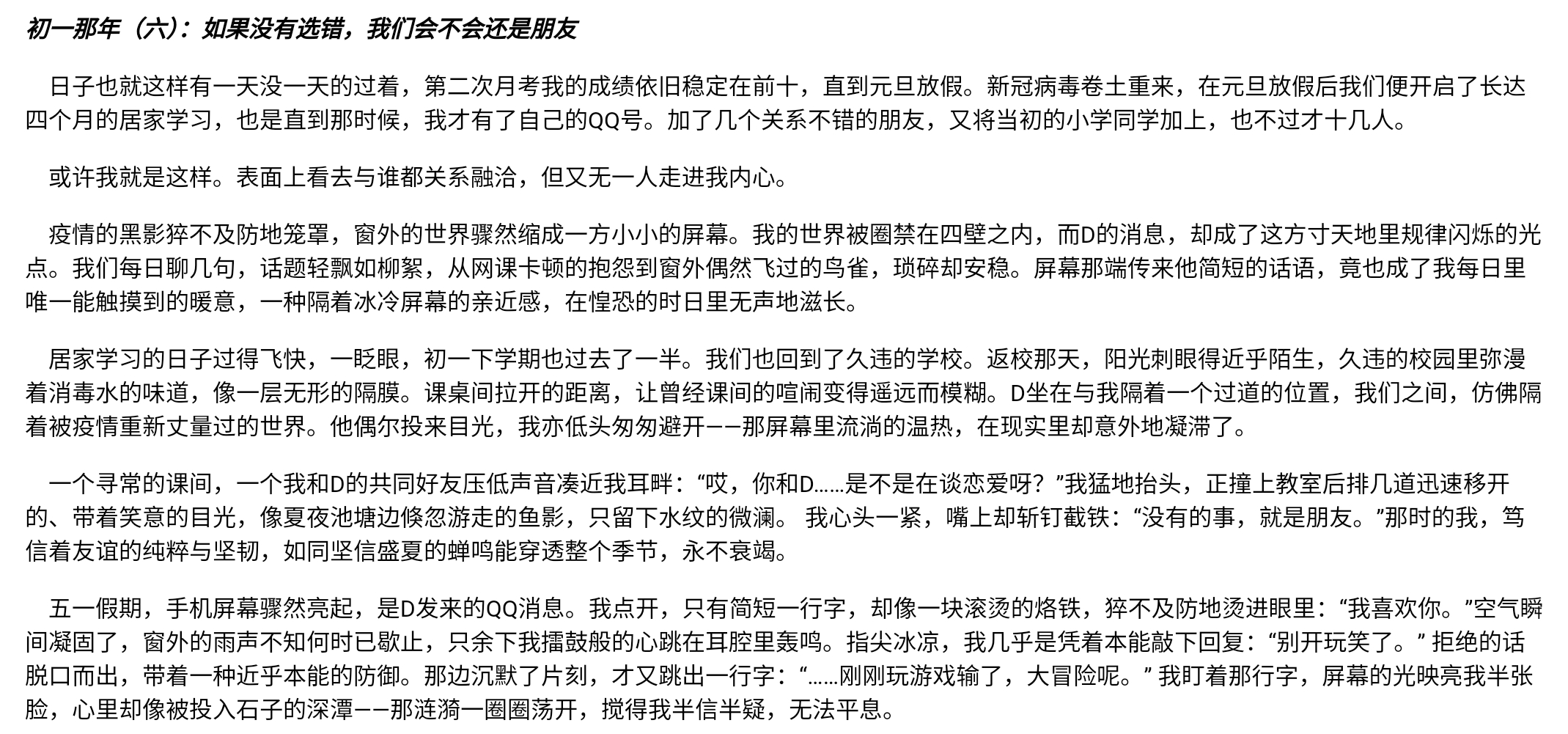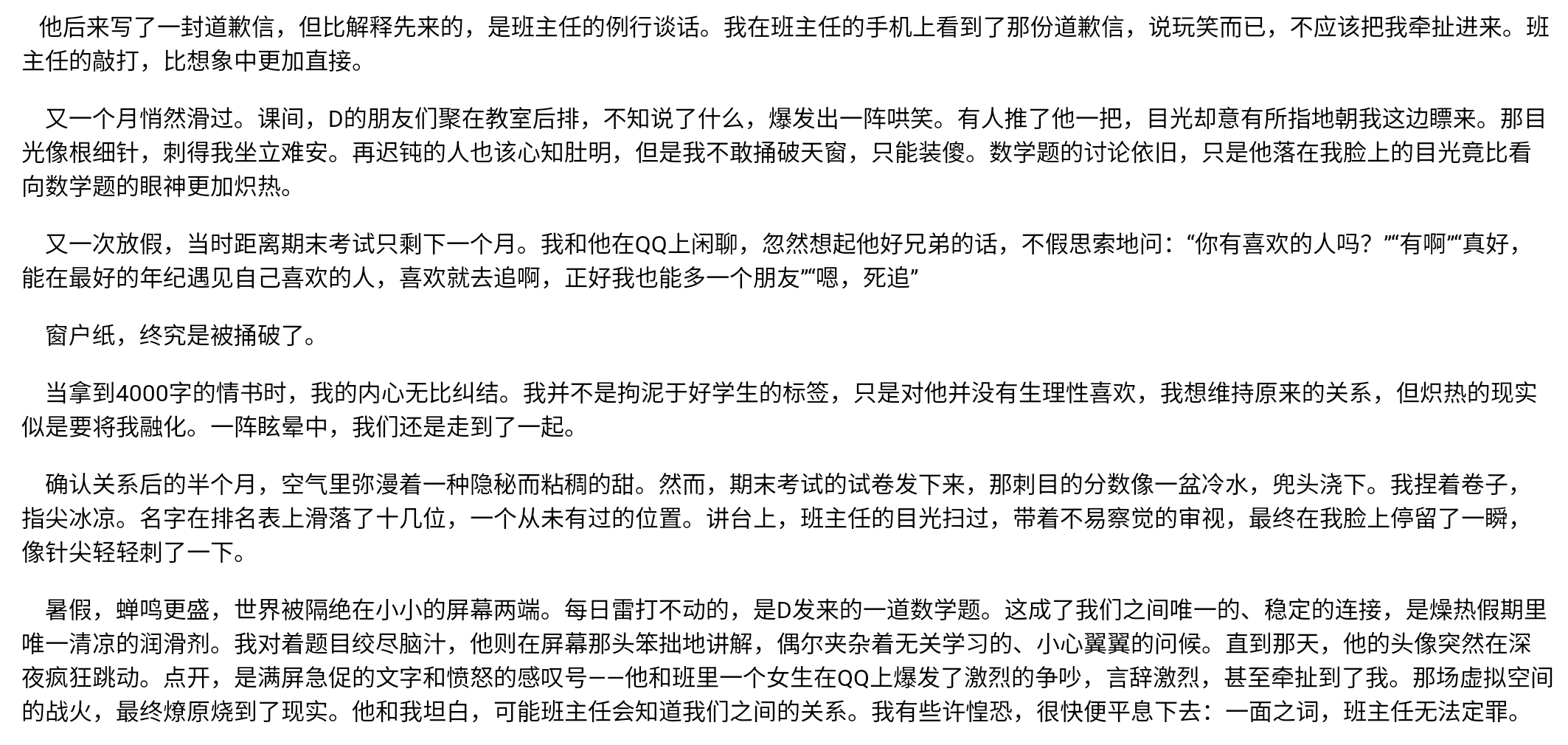- 时间正序
- 时间倒序
- 评论最多
(我讨厌沙发侠😡)
前言
想写这篇文章已经很久了,每每提笔却又不知该像何处落去。一次又一次地感概与他人文笔之精湛,经历之独特,感悟之深邃,只恨我这一身武功无处可用。当真无处可用吗?即使自己的故事那般的平平无奇,似白水般无味,可内心深处早已千百次地预演该如何开头,如何转折,只是从未预想过结局如何,又有谁知道命运的列车未来会驶向何方呢?
抹去千变万化的构思,放弃华丽辞藻的堆砌,我一头扎进这四年无穷的回忆。最终还是决定用最朴素的文字,最平实的语言,勾勒出自己过去的身形。
于是,写吧。
小引:我的人生,从不后悔
听到挚友对我的评价“ghy,你变了”,我默然:“人哪有不变的,我在变,你也一样,我们连被告知的权力都没有,就已经面目全非。你知道的,从踏入明升(我的初中)开始,我的人生就脱离了既定轨道。原计划中,我们本不会相遇。”
我们不再说话,默默举起手中的cocktails,抿了一口酒,酸甜中带着一丝微苦,在舌尖蔓延开来,像极了青春里那些猝不及防的滋味。杯中的冰块发出一声细微的“咔哒”轻响,仿佛时光齿轮又悄然转动了一格。
良久,她的声音似从远方传来:“这四年,你后悔吗?”食指无意识地在杯口打转,明知她已微醺却仍固执地要她回答:“要后悔吗?如果你是我,这四年,你后悔吗?”“那我后悔的东西可多了去了,后悔在明升度过三年,后悔转竞,后悔认识D和W,后悔当初对H那么好却……你的人生本不该这样啊,你生来是属于大场面的。难道,难道你不后悔吗?”她兀然站起攥紧我的手腕,我感到体内的肾上腺素和内啡肽直冲大脑,我掰开她的手,冰冷的双手抚上她炙热的脸颊,手上的高温触感以及手腕的肿痛告诉我一切的真实性,看着她游离的眼神,我一字一顿地说道:“从未后悔,neither in the past, nor at present, nor ever.”我知道,我不是说给她听的,而是告诉自己的心魔,我从不后悔。
- 1
初一那年(二):我就是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
那时我在班上的位置,还是有些许尴尬:班长一人独揽大权,在老师面前百般展现,我不屑于与她争权,但我讨厌被人管束;而她,可能早已将我当成假想敌了吧。班上无一人与我交心,最好的朋友L在另一个班,初二要考来我们班她必须有更多地付出,我不敢多加打扰。但是率先与她针尖对麦芒的并不是我,而是纪律委员Z,一个心比天高的女生。那把火,起初只在Z和H之间噼啪作响。H喜欢掌控着一切,而我只需要认清自己“吉祥物”的身份便可保持中立,Z对H近乎专断的班级管理方式早就憋着一肚子气。自习课按理是Z坐班,可是身为班长的H不愿放权,于是便有了一班两主的景象。我抛却自己副班长的身份,心安理得的戴上耳塞,一头扎进书堆,对现在的我来说,期中考试回归本位才是头等大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人对权力如此看重,可是两人作为硬通货的排名也只能屈居于市150名,在这个高手如云的班级里,这样的成绩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自然班上的各位对这两人也只是貌恭而不心服。
有意思的是,Z是我的小学同学,靠着加倍的努力和成堆的试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当初中所有人的学习时间都被拉长后,她的名字在成绩单上肉眼可见地下滑。当然,小学时,作为副班长的她自然看不惯我这个班长——一个在她眼里靠父母拥有一切的关系户。
我冷眼旁观,乐得清闲。她们斗她们的,我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专注于自己的事。H的锋芒被Z分去大半,投向我的、那种带着审视和防备的目光似乎也少了一些。我甚至有些恶趣味地想,让她们斗得更猛烈些吧。
然而,平静只是假象。H的“统治”基础远比Z想象的要牢固。她是老师的绝对心腹,组织活动也滴水不漏。Z的几次挑战,要么被H用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挡回,要么被老师一句“听班长的”轻飘飘化解。Z的挫败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她的锋芒开始变得有些急躁,甚至有些无理取闹。
那天下午的自习课成了导火索。Z的同桌和前桌因为一道数学题低声争论了几句,声音其实不大。坐在讲台前的H立刻抬起头,目光锐利地扫过去,敲了敲桌子:“安静!自习纪律还要我强调多少遍?” H像是终于找到了爆发点,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服:“班长,讨论问题也不行吗?我们是学生,不是犯人!只要不打扰别人,就不用提醒,你的提醒反而扰乱了同学们的思考。”两人都端坐在讲台上,似乎无事发生,但是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儿已经弥漫了整个教室。我悄悄摘下耳塞,饶有兴致地看着这预料中的一切,只是这一切发生得太早,我以为两人之间的暗流涌动至少会持续到期中考试之后。啧啧,Z还是耐不住性子。
“Z同学,作为班长,我有责任确保班级整体氛围和秩序。你的‘自由’尺度放得太宽,容易失控。” H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却毫无温度。 “失控?你是指没有达到你预想中那种‘表演’给老师看的完美状态吧?” Z的讽刺毫不掩饰。 教室里一片死寂,所有同学都低着头,耳朵却竖得老高。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硝烟。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指尖无意识地转着一支笔,目光落在摊开的书本上,仿佛对眼前的交锋毫无兴趣。但她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语气中的锋芒,都清晰地落入我的感知。
笔尖在试卷上划无意义的符号。讲台边的低气压仍在持续。我看着H强撑的微笑和Z冷硬的侧脸,心中一片清明。 这把火,烧得越旺越好。烧掉H那层精心维护的假面,烧掉Z那过盛的锐气,也烧掉这班级表面平静下的虚伪。我不怕火,我厌恶的只是那令人窒息的浓烟和被强行套上的枷锁。
教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逡巡。H的脸色沉了下来,她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纪律委员,维持课堂秩序是你的职责。他们刚才的行为已经影响了周围同学,请你履行职责,而不是带头质疑规则。” “规则?”Z嗤笑一声,“你的规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副班长,”她突然把矛头转向一直沉默的我,“你说说看,刚才那点声音算违纪吗?班长是不是管得太过了?” 嗡——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我心底暗骂一声,这把火,终究还是精准地烧到了我的脚下。Z这是拉我下水,逼我站队。H也立刻看向我,眼神复杂,有探究,有警告,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成了风暴眼。一边是咄咄逼人、想拉我当盟友的Z;一边是表面冷静、实则等待我“表态”的H。我讨厌被卷入,更讨厌被当作棋子。但此刻,沉默不再是盾牌。我缓缓抬起头,迎向H的目光,又瞥了一眼满脸期待的Z。教室里的寂静沉重得让人窒息,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都意味着选边。这把火,终究要把我置于何处?是继续独善其身,还是被迫卷入这场愈演愈烈的权力漩涡?我的回答,或许将决定这场戏码的走向。
不许走,留下来多陪陪我们呗
雾姐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至少心不坏
至少也乐意陪我这个癫子
要走的话也拦不住的
哼,可笑,即使他可以扭转时间,但他总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突然想起来这句话
所以说,只能祝姐姐以后很好了,至少羡慕一下姐姐在现实当中拥有的友情
你鬼可全部都是在网上了也实属着实羡慕了
手机一没就纯属完蛋
那祝姐姐以后喜结良缘喽,剩下的祝福,等我看情况能不能拿到我手机再说吧

双面祝福!拜拜姐姐
初一那年(四):故事的开始,总是这样
是D。
他斜靠在椅背上,校服外套随意敞着,一条腿甚至伸到了过道里。他脸上挂着那种标志性的、玩世不恭的痞笑,眼神里充满了看戏般的兴味和毫不掩饰的鄙夷。D,老师眼里的“问题生”,随心所欲,不服管教,成绩中等,在班级里一直是个游离的存在,像一颗无法预测轨迹的流星。他从不屑于参与班委的“权力游戏”,对H的权威、Z的铁腕向来嗤之以鼻。今天,是他首次主动向Z和H这两位班委的核心人物开火,而且一出手就是如此辛辣、如此精准的群嘲。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短短七个字,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Z和H精心构建的“权力之争”的严肃外衣,将其瞬间降格为一场供人取乐的“闹剧”。它抹平了班长、副班长、纪律委员的身份差异,将我们三人强行归入“吵闹的女人”这一带着性别偏见的贬义标签下。这不仅是攻击,更是对整个班委权威体系赤裸裸的蔑视和挑衅。
H的脸“腾”地一下红透了,那是一种混合着被羞辱的愤怒和权威被践踏的惊愕。她精心维持的班长形象,在D的轻描淡写中被撕得粉碎。Z更是气得浑身发抖,她最引以为傲的铁面无私和纪律权威,在D的眼里竟成了“唱戏”?她猛地转向D,眼神凶狠得像要把他生吞活剥:“D!你说什么?自习课喧哗,顶撞班委,你……” “我?” D夸张地挑了挑眉,甚至故意打了个哈欠,“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你们三个在上面演得这么投入,还不许观众点评两句?” 他完全无视Z的怒火,反而把腿翘得更高了,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混不吝模样。
火力,瞬间发生了偏移。
前一秒还针锋相对的Z和H,此刻竟然被D的嘲讽强行“绑定”在了一起,共同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她们之间那点关于“规则尺度”的分歧,在D无差别的、极具侮辱性的“唱戏论”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可笑。她们精心构建的对立格局,却被D这个“局外人”用一句轻飘飘的俚语彻底搅乱、打碎。 我站在风暴的中心,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心中那点被卷入的郁气反而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荒诞的清晰感。D的出现,像一块投入精密仪器中的顽石,粗暴地打乱了所有预设的程序。他不在乎规则,不在乎权威,他的“开火”纯粹出于一种对“表演”的厌倦和对“装腔作势”的本能反感。他无意中,用一种最粗暴的方式,验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她们争的,很多时候并非“做事”,而是“做戏”。
教室彻底炸开了锅。窃窃私语声四起,有人惊愕,有人觉得解气,有人纯粹看热闹。H和Z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们互相看了一眼,眼中竟有了一丝同仇敌忾的意味——虽然这“敌”是D。但她们此刻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继续争吵?只会坐实D的“唱戏”说。立刻去镇压D?D那副滚刀肉的样子,恐怕只会让场面更难堪。
我悄然坐回座位,重新拿起笔。漩涡的中心,已经彻底转移。D的出现,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原本由Z和H主导的权力游戏冲刷得七零八落。而风暴过后,谁会真正留下印记?是依旧愤怒却失语的H和Z?是搅动风云后依旧满不在乎的D?还是……那个在风暴的真空区,始终未被真正卷入,并被D的莽撞意外“解围”的我?
无为,有时并非不作为,而是在风暴席卷时,恰好站在了不被裹挟的位置。D的轻蔑,无意中成了对我“不争”立场最有力的注解——当别人在台上“唱戏”时,真正的价值,往往在台下沉静的角落悄然生长。只是这一次,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打破僵局的,竟会是这样一颗“顽石”。
现在想来,那时的H还是不够成熟,竟然在沉默之后选择了硬刚:“我是班长你是班长?!想清楚了吗就说话?要不然这个班长你来当?啊?”“只怕班长不放权呵。”又一次的,H因为这句话脸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我怎么会不放权,来,你上来,剩下的一节课你来管!”本是一句赌气之语,不加理睬便可翻篇,但D却站上了讲台,组织同学自习。
Z也识趣地回到了自己位置,只剩下H一人无所适从地站在那里。直到,摔门而出。
下课之后H也回来了,只是脸上的泪痕遮掩不住。剩下的一节课纪律出奇得好,虽不能说是D的功劳,却也变相地在H的脸上落下了鲜红的巴掌印。我看向D的眼神中少了几分抵触,多了一丝探究与玩味,却不料,眼神在空气中交汇,而两个人都没有躲闪。
班主任出差的第一天,就如此有趣。这个班,真的没让我失望啊。
初中同为副班长,只能说我们班长一个男生,足有八百个心眼,
(我们班除了班长,其他的主要职务都是一男一女各一个)
我经常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和另一个副班长斗嘴,
他们似乎很喜欢勾心斗角,但我觉得有啥目的直接说不就好了
再看纪律委员,男纪律委员是我哥们,他的管理极其严格,但他似乎不是为了权力,而是对规则的敬重,他不允许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发生;
女纪律委员呢?她似乎和班长站一队,她似乎对任何事都有一票否决权,而每次在背后支持的,便是班长……
他们反正再咋勾心斗角也勾不到我这个没有心的人身上,
就算有跟我过不去的人,那有什么是物理手段不能解决的?
我倒像是个见证者,见证着班级管理层的腐败,见证新来班主任的唯成绩论……
我那位纪律委员哥们则是没忍住爱情的诱惑,和美丽的语文课代表携手公然打破他所尊敬的规则,最后另一位纪律委员和班长都跟着他去了。
现在看来这一切就像是场闹剧,
但他们结局似乎都还可以,学业友情爱情多丰收呢
而我,似乎除了一纸录取通知书外一无所有……
初一那年(五):热爱本身,就是目的
两天之后,班主任回归,自然已经听说了这场闹剧。他罢免了Z纪律委员一职,对D和H进行了口头批评,让他们将重心放在学习上。H仍不服气,但班主任转头将班长的权力分给我一半,我知道,这一次,我已无从可逃。我遇上H充满敌意的目光,只是轻轻一笑:我不和你争,但,是我的,只能是我的。
回归副班长本职,自然少不了与不稳定因素D打交道:上课埋头苦干小蓝本,作业随心所欲,对规则嗤之以鼻。几次当众的“管理”与“被挑衅”,让我们几乎成了公开的对头。他看我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戏谑,仿佛在嘲笑我这副“好学生”的壳子下,也不过是颗被排名和规则驯化的心。而我一次次地将他的大名写入管理记载本。
直到那节数学课。
老师抛出一道极其刁钻的组合数学题,其实只是想打击一下我们的自信心,并未指望有人能够解出(当时班上一堆人整天研究小篮本,以致任课老师在班主任面前大倒苦水,班主任便想请数学老师驯化我们)。教室里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绞尽脑汁,思路却像打结的毛线团。就在老师准备揭晓答案时,角落里响起一个懒洋洋却异常清晰的声音:“用染色模型,分奇偶情况讨论试试?” 我猛地抬头,撞上D的目光。他没有看我,只是随手在草稿纸上画了几个圈圈点点,思路却如刀锋般锐利,瞬间劈开了迷雾。他寥寥数语,竟比老师冗长的讲解更直指核心。那一刻,我心中的敌意被一种强烈的、纯粹的震撼取代——原来,在这副玩世不恭的表象下,藏着如此耀眼的光芒。
课后,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他座位旁,指着那道题:“你刚才说的奇偶分类,能再详细讲讲吗?”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换上那副惯有的、带着点痞气的笑容:“哟,副班长大人也对这个感兴趣?”但语气里,少了几分嘲讽,多了点棋逢对手的兴致。
数竞,成了我们之间奇妙的润滑剂。
在那些啃难题、争论解法、分享思路的课间,我们抛开了“副班长”和“问题生”的身份,只剩下两个被数学之美深深吸引的灵魂。我发现,D对数学的热爱,纯粹得令人嫉妒。他不为竞赛加分,不为升学保送,甚至不在乎老师是否认可。他解题,只因为“好玩”,因为“想看看它到底能有多美”。这种近乎本能的、不掺杂质的热情,像一道强光,穿透了我心中弥漫的迷雾。
“你干嘛把自己逼那么紧?”有一次,我们啃完一道难题,他靠在后桌的桌沿上,懒懒地说,“排名?那玩意儿跟数学本身有关系吗?就像欣赏一幅画,非得知道它值多少钱才能觉得它美吗?”他随手撕下我贴在桌角提醒自己的期中考排名目标,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烦不烦。”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漾开一圈圈涟漪。我长久以来的挣扎,不正是因为我赋予了数竞太多“意义”和“责任”吗?它必须成为通往顶尖大学的阶梯,必须证明我的能力,必须洗刷“关系户”的标签……这些沉重的包袱,早已压弯了它本应轻盈灵动的翅膀。 看着D解题时眼中闪烁的、近乎孩童般纯粹的光,我笑了。
那个周末,我和父母进行了一次长谈。不再是诉苦成绩的压力,而是坦诚地分享了我的迷茫、D带给我的触动,以及我对数学那份割舍不掉却也不想再被其绑架的热爱。我告诉他们,我想重新定位:数竞,是我珍视的兴趣爱好,是思维的体操,是疲惫课业后的精神花园,而非必须争夺的战场。 我希望将主要精力回归课内,夯实基础,但请求他们允许我保留这份“奢侈”的爱好。 父母沉默了片刻,眼中是理解和欣慰。他们没有责备我的“退步”,反而为我终于找到内心的平衡点而高兴。“好,”父亲拍拍我的肩,“既然是你真正想做的,我们支持。兴趣需要土壤才能生长。”
很快,他们为我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一对一老师。但这不再是“升学助力”的压力源,而是纯粹为了满足我的求知欲和乐趣,像请了一位可以深入探讨艺术的朋友。 放下那份“必须用数学证明什么”的执念,世界豁然开朗。我不再焦虑于投入的时间是否“浪费”,不再在课内学习时分心惦记着未解的难题。当数学回归纯粹的爱好,它反而成了高效学习后最好的放松和奖赏。
辅导老师的课,成了每周最期待的时刻,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探索和享受思维的乐趣。
同时,没有了心理负担,课内学习变得前所未有的专注和高效。我不再纠结于“为什么学”,而是沉浸于“如何学得更好”。那些曾经觉得枯燥的知识点,因为心态的平和,反而显露出它们内在的逻辑和美感。原来,专注本身就有力量。
期中考试如期而至。走进考场时,我的心境是前所未有的平静。没有了对排名的患得患失,没有了“必须证明自己”的沉重包袱。我只是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像解开一个个有趣的谜题。 成绩揭晓那天,我重新回到了年级前十的位置。教室里响起一些惊讶的低语和目光。但这一次,我心中没有狂喜,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坦然。我知道,这份成绩不再是某种光环或证明,它只是我内心平静、专注投入后的自然结果。它证明的不是我的天赋或背景,而是选择的力量——选择接纳自己的热爱,也选择承担当下的责任;选择放下无谓的包袱,也选择脚踏实地的前行。 课间,D晃悠过来,扫了一眼贴在墙上的排名表,嘴角勾起他标志性的、带着点玩味的笑:“哟,副班长,回归原位了?” 他的眼神里没有嫉妒,也没有嘲讽,只有一丝了然和……也许是一点点为朋友感到的轻松?
评价是男女比例太均衡导致的
《当你的班上男女比例高达17:1》
正常恋爱早在高一就绝迹了,现在你去问我们班有没有xql不如问我们班有没有南通,答案可能还会理想一点♿♿♿
你说隔壁班?开玩笑全年级乃至全校都知道竞赛班可是全校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班级🤣一个在其他人眼里留长发离群沉默寡言的男生看起来是奇怪的,不好接近的。但是在我们班他已经算是很正常了,就算让我们找出他有哪里不正常估计我们都会想半天🤗🤗🤗其他的入诸如初中的时候拥有几十个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和十几对暧昧关系以及至少5个已经承认的npy的黑皮准体育生,只会爆算的数竞男(除了爆算啥都不会,EQ为负值),一下课就开始C边上xnn的(疑似)南通物竞生等等,之前还有叠罗汉(没错就是如你所想,声音非常大,把隔壁的两个高考培优班全吸引过来了),击剑(卷子太多折/捆的纸剑,最后基本上都打断了)诸如此类的小游戏。。。可想而知我们班什么形象,跨班的估计不是有着足够的信念就是来猎奇的♿♿♿